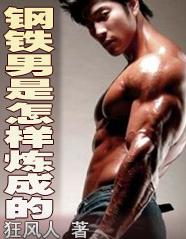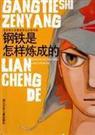钢铁雄心之舰男穿越记-第37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的“革命浪漫主义者”。
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他们的立场、主张、作为,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革命党”时所用的话,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如将贵族替换成“高种姓的革命者”,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僧侣、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
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英属印度的境内,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一边继续进行“和平闹事”,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立建国。另一边,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却东、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在打击印共一事上,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
“被英国人殖民,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被布尔什维克解放,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
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
在宣传上,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指责他们“分裂印度”,无耻的“强盗和流氓”。
1940年后,英国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控制区内印共的打击力度,在过这程中,印度国内的许多党派和英国人暗中通气,提供情报,印共在英属印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当然,这些印度的诸多党派,倒也有聪明人,懂得玩两面三刀的把戏。他们和英国人的合作打击印共,不少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象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作为印度最大的党派,他们一方面和英国人暗中联系泄露印共的活动情,另一方面却也偷偷地联系苏联人和中国,而自身在印度表面,却摆出不发一言的伪中立嘴脸。
不过这些党派的两面三刀的嘴脸,很快通过阿尔托利娅传到了林汉这边,然后又传到中方那边。
中方上层本来还存在着一些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但在拿到林汉传来的情报,看清了印度这伙人的嘴脸之后,哪怕是再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也被刺激得愤怒起来。
印度境内各大分离主义政党的嘴脸和本质,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全看在眼里,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让人在当地上层中炒作“布尔什维克瘟疫威胁论”,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权因为抗拒和恐惧“赤化”而不敢脱离英国政府的保护。1940年休战之时,受到美国的威胁,加上战争中损失惨重,英国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点,但是他们还是撑了过来,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度当地的中层和上层,害怕独立后失去英国的保护,让东边和西边的红色势力入侵变色而失去一切。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上,印度中上层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
一年战争结束后,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为了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力,打着“反对布什维克化”的旗号,在印度组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
这支所谓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其本质上,和苏联建国战争时的“白军”差不多,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个土邦的头领提供资金,英国人提供武器和军官,组建的目的,就是一旦中苏两家再度对印度发动战争时,就由支同盟军顶到前线去当炮灰。
这是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在战后三年里采取的应对方针。
而阿尔托出现后,意识到其“神使”的身份,通过宗教给印度洗脑的巨大好处后,英国官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从1935年起,英国人在中国就遭遇了红色中国的士兵。
在那场战争中,英国战败,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战争过程中,那些“红色布尔什维克”在战场的英勇无畏的作战意志,尤其是在舟山群岛上的苦苦坚持了一年游击战,伤亡超过七成却不肯投降,最后以胜利者身份离开的中方游击队员,给英国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狂战士”,这是战后英国参战军人给对手打出的评价。
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那一套理论的理解比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他们在宣传上攻击对手时,就很爱用这是一支“宗教式狂热的军队”。
虽然英国政府这么“宗教式军队”攻击对手,但实则心里充满了酸溜溜的味道,他们心里也很想建立一支类似的军队。
著名的“英奸”丘吉尔在曾在战争期间说过一句很无耻的话: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死光之前,大英帝国都不会与德国和谈。
印度有两亿人口,由印度征召的殖民地军队是英国陆军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印度阿三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南亚次大陆这片大陆的民风实在太不够尚武了,根本就不是“战斗的民族”——如果足够尚武,就不至于几千年的历史,只要异族打进来,总能轻易地征服他们,谁都可过来上他们。
英国政府最大的梦想就是,只要从这两亿人口中征得的士兵,能拥有廓尔喀的士兵一样的作战意志,那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就永远不落。廓尔喀人,是印度人中战斗力最强的民族,由该族征得的士兵战斗意志很让英国人满意,唯一遗憾的是该族的人口不多,能征得的兵源有限。
除了廓尔喀人外,印度这儿的其他民族,其战斗力普遍可以用战五渣来形容。以至于一年战争中,在面对中苏两家的东西围攻中,英国空有两亿兵源的殖民地和主场优势,却无力组织起强力的军队对抗。
阿尔托利娅出现后,英国人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英国官方的一个“奇思妙想”就是,借助阿尔托利娅的“神使”,组建一支“宗教化”的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作战意志不成问题,是极好用的炮灰。
在埃及传教成功后,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英国政府想通过她,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
第471章荣誉布列塔尼亚人和圣战士
哈里生于印度中部安得拉邦一个名叫瓦里维杜的小村庄,该村有200多户人家。这些人家被一堵墙从中隔开,这堵墙虽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整齐,但它发挥着当年“柏林墙”的作用。墙左右半公里都是空地,作为墙两边人们交往的“缓冲地带”。住在墙南边的人家属于高种姓“婆罗门”,住在墙北边的人家属于“贱民”。哈里博士就出生在墙北边。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社会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为第三种姓,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为第四种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被高种姓当作奴隶来用。
四大种姓之外,还有很多印度人,他们连成为首陀罗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被称做“阿丘得”,意思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洁的,谁要是接触了他们,即便是接触了他们的身影,谁便会受到玷污。最好连想都不要想,一想,脑子便被污染了。
在英属印度,贱民的总数约占人口比例的百分十五,在印度,贱民宁愿叫自己为“达利特”,意思是受压迫的人。
哈里从小就极其痛恨印度罪恶的种姓制度,由于种姓是世袭的,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哈里便注定是一个贱民。他从小耳闻目睹达利特人遭受的社会压迫。高种姓的人之所以让他们住在北边,是因为风经常从南向北刮,河里的水也是从南往北流,这样高种姓的人就感觉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会被污染。
“村子里的一切资源,包括土地和水,都属于高种姓家族,我们达利特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无尽的屈辱。”
达利特人能做的只是扫大街、扫厕所和处理动物尸体。不洁的工作更加重了人们对达利特人不洁的印象,高种姓人躲避达利特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他们不能去村里的寺庙祈祷,也不能到公共水井去挑水。不仅如此,为了与高种姓人保持距离,他们还要在口里含一个口哨,不断吹着,提醒他们及早躲避,另外还要在屁股上绑一片很大的能拖到地面的棕榈树叶,及时清扫走过的脚印。
对于印度的“达利特人”来说,“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制度”的马列毛革命理论,简直就是他们量身订作的。
当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英属印度渗透时,和军队一起送过来的,还有打碎旧社会旧秩序的革命思想。
比起来自北方的红色军队,英国人害怕的是红色思想在印度漫延,尤其是“贱民”中间漫延。
所以1941年停战后,英国人和当地的印度中上层联起手来,拼命地抑制“红色思想”在印度底层漫延,甚至不惜动用了军警、地方宗族势力以及绞刑架。
而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后,英国官方的一个“奇思妙想”就是,借助阿尔托利娅的“神使”,组建一支“宗教化”的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作战意志不成问题,是极好用的炮灰。
在埃及传教成功后,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英国政府想通过她,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
而英国人引入军队的宗教,自然就是英国的国教。
历史上,英国人虽然早早地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活动增加,然而,如同其他非印度教的宗教一样,基督教在印度亦受到主流宗教的敌视和排斥。
过去的两百年时间里,印度人用蹩脚的英语这样描述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过程:基督教是恶魔的宗教,基督徒大量饮酒,做过很多坏事,基督徒是毁灭的同义词。
早期的基督传播是受到印度中上层极大的抵制,唯有底层走投无路的人,比如贱民,首陀罗,才会去信奉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两个分支,天主教在传教时,为了获得当地上层的支持,不惜将自己“印教教”化,在穿着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和宗教仪式上都模仿当地的印度教,甚至自称为西方的婆罗门。不仅如此,他们还延续了当地印度教的各类陋习,比如童婚、萨提制等等,最关键的是,不同种姓的信徒在不同的教堂祈祷,吃不同的圣餐,甚至在不同的井水里洗手等等,简直可以称之为披着基督皮的婆罗门。
而新教,包括英国的国教,在这一点上要比天主教进步得多。他们直接向印度人宣传“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他是非人道罪恶的制度,由此得到了印度下层人民的支持,甚至还因此推动了印度教自身的改革。
不过英国国教在印度传教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官方也以默许和暗中支持态度鼓励其在印度传播,但其影响力,主要也维持在印度地区沿海一代的较发达城市,并未过多的深入内陆。
主要原因一是印度内陆较为落后,当地土邦王公和土著宗教力量对这种侵犯自己利益的宗教本能地抵制,二是官方也担心引发不必要的宗教冲突,影响英国对印度的统制力度。加上过去历史上印度人因为子弹涂牛油猪脂和信仰冲突的原因,发生大规模的兵变起义,英国官方对宗教问题引发的再次兵变心有余悸,所以这方面也采取了相对消极的“中立”态度。
1940欧洲战争结束后,印度地区的分离势力再次抬头,虽然英国政府靠着鼓吹“布尔什维克威胁论”暂时压制住了蠢蠢欲动的当地土邦王公。但是英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在印度问题上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