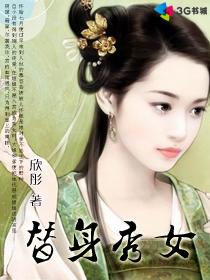沉重的肉身-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哪抗舛哉庋纳槠渎旃酥椋骸 ∥蚁不豆鄄焐乃槠不对诓恢耙蚝蠊那榭鱿屡南卤晃揖枰黄车纳睢! °B壑械陌褪侵站恳饽哑剑牡谝桓龊迨歉鎏迳娜惹楹屠硐搿歉龇且不冻璨豢傻呐⒆拥男脑浮! ∮捎诟鎏迮荚诘娜馍硇裕脑谛跃褪撬槠! ⊙堑焙拖耐拮叱鲆恋樵埃推扑榱耍诖耸乐邪偷酶试赋晌槠0褪嵌猿晌槠纳惹楹屠硐胗行判暮团瓮运郎换凇! °B壑械陌牡诙龊迨窃阢B廴松械陌莺腿棠停磺崾用恳豢旁谏踉衅扑榈男模豢湔抛约旱纳胂蟮氖苌耍辶旅恳桓鲈谏恼踉谐晌乃槠纳! ≈炖鲆墩业阶约赫煞虻那槿耍挥性鸨福蛞蟾星榕獬ィ颜煞蛩械囊挪婵詈鸵欢奥シ俊桓! ≈炖鲆恫辉偬永耄敲娑宰约旱墓ァK煳虻剑竦们楦械淖杂尚枰硪恢职哪芰Α! ≈炖鲆锻O卵扒笞匀蝗ɡ淖杂傻慕挪剑蛔碜呦虬捕贸さ押透智俚亩源鹌仔辞胺蛭赐瓿傻慕幌烨谡獠棵芭分蕖钡慕幌炖种校孤宸蛩够⑷肓俗约憾哉饬硪恢职哪芰Φ男判摹K楣沽艘晃幻蠽an den 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 You know how much he loved him。 Not just because of his music; but because of his tragic life and his premonition of misery。 另一种爱的能力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 《蓝、白、红》三部曲中,只有《蓝》的结局没有意外事件,基斯洛夫斯基用保罗的爱颂来祝福朱丽叶: 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如果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是坚韧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保罗,《科林多前书》13:1—2,4,7—8,13)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心中的另一种爱的能力。 保罗的爱颂在《蓝》的结局以合唱和独唱形式出现,用古希腊文演唱,旋律有如一曲悲戚颂歌——颂唱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在这恍如隔世之音的悲戚颂歌中,基斯洛夫斯基寄托了自己对欧洲和世界的信、望、爱: The rhythm is slower and from the music of the joyous hymn about love which could be the salvation of Europe and of the world; it becomes serious; announces something dark; dangerous。 与此同时,基斯洛夫斯基让人们在画面上看到:By the window; we find Julie; her face in her hands。 One by one; tears appear on these hands。 Julie is crying helplessly。 一位美国评论家说,基斯洛夫斯基是“幽默的虚无主义者”。如此评论表明这位美国评论家何等缺乏评鉴能力。“幽默的虚无主义者”这个称号用于昆德拉倒恰如其分,他的叙事沉醉于幽默,很少让人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作品是一个隐喻的织体,不少人物在各个作品中交错出场。生活是偶在的网络,道德意识是这张布满尘灰的网上的蜘蛛。他的道德焦虑不是律法主义的或决疑论的。生命的道德不是黑白分明,也非雾霭迷蒙,而是悖论中的爱的蔚蓝色。一个个体的生命是由一连串偶然聚合而成的,个体没有一个恒在的依持,个体幸福是残缺的,个体的爱也是破损的,在偶然中成为碎片。 尽管如此,基斯洛夫斯基固执地要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珍惜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绝不仅仅为了展示爱的碎片,他记述过两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她现在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斯洛夫斯基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这女人与她女儿虽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俩一同看了《十诫》,看完电视后,女儿吻了母亲一下。 “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基斯洛夫斯基这样觉得。 基斯洛夫斯基并非不清楚,“这个吻的爱只持续了五分钟”。尽管如此,只为这一个只有五分钟的吻,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也值了。 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却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碎片。 这种珍惜是一种信念——蔚蓝色的信念。 我告诉小林,这是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令我深深怀念。
无法追究的个人性情?(《十诫》之五)
波兰实行军管后,基斯洛夫斯基拍了两部电影(《盲目的机遇》和《永无休止》),都被军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禁映。 一天,基斯洛夫斯基心情沮丧,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天色也显得沮丧,下着雨。在一个拐角处,基斯洛夫斯基迎面撞上好久不见的政治诉讼律师皮斯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 几年前,基斯洛夫斯基在法庭拍一部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纪录片,认识了当时为“反革命分子”担任辩护律师的皮斯维茨,俩人成了好朋友。《永无休止》的电影脚本就是他们俩合作的结果。 那天,皮斯维茨的心情碰巧也不好。俩人闲聊了几句,皮斯维茨没头没脑地对基斯洛夫斯基说:“该有人拍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那就是你。” 电视系列作品《十诫》 的创意就是从这两个人在大街上邂逅产生出来的,相当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说,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不会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他们俩心情都不好,也不会有《十诫》。 这部在东欧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产生的作品问世后,西欧影视文化界称为十余年来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诫的电影版获第一届欧洲影展首奖)。我以为,这部作品也应该算是当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诫》出自两个人在一个下雨天的沮丧心绪。为了什么沮丧?因为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被禁?因为皮斯维茨老是为人民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显然不是。作品被禁或因为“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这两个人老早就习惯了,要说沮丧,也早就沮丧过了。 这两个人的沮丧是因为人民民主社会中人的道德意识状况,基斯洛夫斯基说得很清楚: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人民民主社会是一个道德一体化的社会,有社群主义者向往的那种共同一致的道德,按理说,人人都是有道德意识的。这两个人在这道德一体化的社会中感到道德意识的冷漠,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听说:“连死都不怕,还怕活?”也许这话正表明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不“怕”死的活是什么样的活? 就让我们从这个问题说起,了解一下死的伦理意识是如何变得冷漠的。 雅泽克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双混浊的目光四处张望,打量着街上的各色行人,显得有些烦躁。 本来,雅泽克今天上街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杀死一个人。他走到街上才发觉自己漫无目的,因为他并没有要杀哪一个人或哪一类人的明确意念,只是要杀一个人,好像要完成一桩形而上的杀人。如果他清楚自己要杀一个商人或者军人或者书生,就不会有眼下的烦躁。 要把杀一个人的一般意念变成具体的杀某一个人的行动,需要一个实际的理由。雅泽克拿着妹妹的相片走进路边一家照相馆冲洗,故意提些刁钻的要求,如果相馆老板发脾气,他就有个理由把她杀了。 相馆老板没有发脾气,雅泽克只得转出来,瞧见路边一个值勤的警察。这是一个好对象,警察平日总无事找他麻烦。雅泽克走进旁边一家餐馆吃快餐,顺便盘算如何下手,一辆警车偏偏在这时开来把值勤的警察接走——他下班了。 雅泽克在街上转久了,觉得尿急,进了公厕。 有个少年在里面,雅泽克把他掀倒在便槽,要是这少年生了气,雅泽克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实现今天要杀一个人的意念了。这个少年偏偏没有生气,只是木呆呆地看着雅泽克,令他下不了手。 雅泽克无意中来到的士站,身边有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叫车,的士司机拒载,雅泽克觉得正好送来了一个杀人理由,他跳上的士,说要去两个酒鬼要去的地方。车到郊外,雅泽克取出准备好的绳子勒司机的脖子,再用榔头击打。司机挣扎,想喊叫,雅泽克越勒越紧,令他喊不出来,只发出“咯、咯、咯”的怪声。过一会没有声了,雅泽克以为已经死了,拖他到河边,又听见他发出咕咕噜噜的求饶声。 雅泽克搬起一块石头猛砸这个人的头,才没有声了。 雅泽克觉得杀一个人真累。 雅泽克的辩护律师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见习律师,人民法庭安排他为雅泽克辩护。自从走进法院那天起,他就觉得,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边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边刀刃是个人性情的具体性。 他学法律本来是为了逃避孤单。好些人以为,生活在人民民主社会不会有孤单,其实不然。许多人都很孤单。人们生活得不诚实,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报纸上经常说“亲如一家”的社会中的孤单。见习律师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以为做律师可以接触各种人,可以避免孤单,变得诚实一些。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都有正面和底面,像一张胶片的两面,生活在这一面的人不大容易同生活在另一面的打照面。司法制度把生活的正面和底面贴在一起,见习律师想通过律师这个行业去接触生活在另一面不太容易见到的人——比如雅泽克这样的人。 见习律师到监房去看雅泽克,了解他杀人的动机。 雅泽克沉默了一阵子,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与妹妹关系最好。她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十分活泼可爱。一天晚上,她被汽车碾死了。开车的司机是雅泽克的熟人,那天他们还一起喝酒。那司机饮酒太多,醉醺醺开车把他妹妹碾死了。 妹妹的死使雅泽克的生活感觉变得晕黄起来,他觉得生活可恨,要找一个人报仇。 “十诫”上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旧约》也记着太多的杀人,甚至要求上主出手杀人。“不可杀人”的诫命实际说的是“不可没有理由地杀人”。有理由的杀人是允许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间断过。雅泽克从小就经常看到一卡车一卡车胸前挂着“反革命犯”牌子的男人女人被拉到河边的沙滩去枪毙,从小就经常看小说和电影中讲杀敌人如何伟大、光荣。 从小看到大,已经习惯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犯人是用步枪子弹打脑袋,有的人民手里捧着一盆清水,等步枪子弹打开脑袋盖后,就跑上去把反革命犯的脑花放在水里过一下趁热吃,说是特别补脑。雅泽克觉得杀人没有什么好惊奇,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正当理由的杀人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颂扬。枪毙一个反革命犯,他的家属还得付子弹费。 谁来决定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 如果有人侵犯和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杀这个人的理由就是正当的了。雅泽克觉得为了自己的妹妹杀一个人是有理由的,为这事他想了好久。他没有想到的是,杀死一个人好难,他用那根工业用的专用绳子勒那司机好久都不死…… 见习律师觉得自己碰到的纯粹是一个个人性情的问题。 见习律师从法学院学到的只是抽象的法理知识,在生活中碰触到的却是人的偶然性情。面临考验的不是运用法理知识处理实际个案的技能,而是运用法理条文的人的良知。雅泽克杀人案让见习律师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信心,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的法理问题:对谁做到公正? 对谁公正是一个伦理问题。 雅泽克妹妹的遭遇是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个这样的不幸者的兄长都会产生要找一个人报复的念头。雅泽克身上有一种暴烈性情,这性情把一桩意外事件感觉成道义事件。可是,他应该为这种性情负责吗?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许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恶。 司法暴力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但它面对的经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惩罚不正当的故意行为,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裂缝。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恶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谁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说,雅泽克的杀人和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同质的,都是有理的杀人。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