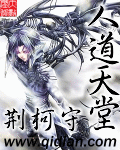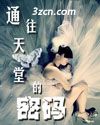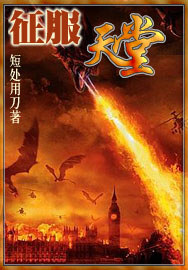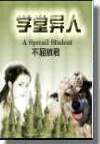女中堂-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惜桐从她的嘴角看见兴灾乐祸的表情;这大奶奶故意要让她下不了台。不怕!她自有办法应付;这时,就该额娘出场了。
“韵沁想要唱首曲子,祝贺老爷寿诞。”额娘还跪在地上,颤声说。
“起来吧,韵沁你唱……”阿玛犹未从她脸上的震撼中回过神,讪讪道。
惜桐站起来,靠在额娘的身边,拉着她的手,状似害怕的样子,其实是坚定地地握一下额娘的手,给她打气,要她安心:别怕!一切有我!
额娘大概是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出现过,所以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不但低着头满脸通红,还身体微颤、手指冰冷。
她这样的表现,果然惹来四周窃窃私语,都可以听见宠妾们的讽笑声了。
很好,反差越大,效果越震撼。她准备好了!心想:周杰伦同志,对不起啊,借用你的‘菊花台’曲,来唱这首曲子。
她深吸口气,张嘴唱出由古人冯惟敏所写的祝寿词,这首词的意境切合阿玛的心境,只是她去掉几句不合适的句子;相信他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鸥盟常共水云亲,鹤算偏宜海屋邻,蜗轩更与蓬莱近。奉身安、行步稳。南极生辉,北海开尊。贤主嘉宾,金昆玉季,桂子兰孙。论宦业、调羹补衮,振家声、善武能文。麟阁功勋,凤藻丝纶,与国同休,奕世承恩。”
虽是五岁女娃儿的娇声,但以她这些年的练习,不论是运气还是发声技巧都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再加上她字正腔圆,所以每一个音色都清楚回荡在整个乐寿堂里。一时之间人人鸦雀无声,静静聆听她的歌声。才唱两句,阿玛瞪大不可置信的眼,一瞬也不瞬地看着身材矮小的她。
惜桐尽情地欢唱,用憋了五年的力气来唱,把这首祝寿曲唱得荡气回肠。曲毕,她规规矩矩地行了个旗礼──抹鬓礼。
霎时,掌声如雷,每个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似乎被她这个小女娃的歌声给震撼到;尤其是那些乐工们,都欢呼着站起来鼓掌了,甚至有人失礼地大声说:“真是太惊人了,从未听过如此纯净甜美的声音!”
阿玛也动容了,眼里有感动的神色,他笑着说:“这是阿玛听过最好听的祝寿曲子,韵沁唱得太好了!”
惜桐看他一副深受感动的模样,再装出很害羞却很高兴的声音说:“沁儿还想再唱一曲给阿玛听,这是沁儿偷偷学额娘自己作的曲子……”
她现在说的这些台词可没和额娘排练过,所以她一说完,额娘立刻现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愣了会儿慌张地拉她往后:“沁儿,不可!”
其实这首曲子不是额娘作的,而是她又借用别人的词曲,在很早以前就教会额娘唱。由于词意相当吻合额娘的心境,所以额娘常常在私下吟唱,她故意在这时候提出,为的是要感动那个负心的阿玛,要他想起有一个女人时常在想念他。
阿玛听到,反而相当开心:“这有什么关系,难得沁儿有这番心意,就让她唱吧!”
额娘慢慢放开拉着她的手,却用满是心思的眼看她,脸上又白又红。
她略为抬头看,再次拉着她的手给她勇气,然后转头看着阿玛,以及旁边满脸不以为意的大奶奶,开始放声唱周杰伦曲、方文山词的“青花瓷”,但为切合额娘的心意,她改动几句: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月柳,一如你初扮。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子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朝霞照人;你的美一缕飘升,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这次惜桐用了所有的感情,还故意略带一点哭腔,营造出一种伤心的氛围。还为了让大家听得清楚,再把拍子拉长,发音更准确;如此一来,词曲中的意境全被她唱出来了,将那股相思的情意,变得更加****深刻而又哀婉动人。
一曲唱完,整堂寂静无声,似乎人人都不敢大声出气,怕惊扰了这美丽感人的氛围。
阿玛的眼眶红了,一双眼睛停留在低着头的额娘头顶上。
看到这一画面,惜桐也想掉泪了;高兴得掉泪,阿玛终于被额娘感动了!
惜桐知道书上曾记载,阿玛非常喜欢有才气的女人,所以大奶奶为他选的小妾都是深具才学的女人;而额娘只因长得不美,并不是没有才学,但要和那些**楼出身的才女,她是比不上;惜桐这才借着方同志的才学,为额娘一圆相思;希望方同志不要在意才好。
“再……再唱一次。”阿玛缓声说道。
她应了声,拉拉额娘的手,指向乐工的方向,意思是要额娘帮她找伴奏的人,立刻有位乐师朝她们点头;他抬来一架古筝、琴几,坐在惜桐身边,先练弹了一下,觉得可以了便朝惜桐点头,于是惜桐开口再唱一次。
这次有了铿锵有力的筝音伴奏,她将音色放软,比刚才更加温柔,唱得歌曲有如空谷传声,余音缭绕不绝如缕,连她自己都十分满意。
“而我在等你……”她用这句词来结束曲子。
曲罢,仍无人出声,每人似还沉浸在词曲的意境里;连大奶奶的脸色都温软下来,略带同情地看一眼额娘。
9 来历(一)
帮她伴奏的乐师站起来朝额娘一礼,说:“小人斗胆,想请问这位姨娘,小人可不可以把这首的词曲记下来,将来演奏?”
惜桐心惊;这不可以,曲子可以弹,但是词句会流传下来,她不可以坏了方同志的未来,所以她不肯答应,便故意扭捏地向乐师细声说:“我额娘说这首词是她专为我阿玛所写,不愿意让人知道,所以她才会那么难堪……”
“沁儿,在说什么,为何不大声说出来?”阿玛问。
她装成很害怕的样子,躲到额娘身后;反正她已经把话传给乐师,再来是他的责任了。
乐师笑呵呵跪地对阿玛说:“小姐刚才说,这首词是她额娘专为老爷所写,不愿意公开,所以不便给小人演奏,但曲子倒是可以。”
阿玛再看头低得不能再低的额娘,眼睛尽是温情蜜意:“那就这样吧。”
“谢老爷!”乐师磕头离去。
“来,沁儿上前,阿玛有赏!”
她拉着额娘的手,才肯上前。只见阿玛从他的怀里,拿出一只白玉镯,向她招手;这白玉镯通体透亮晶莹,光泽圆润;最奇的是整只透白的玉镯里,竟然有一个颜色漂亮异常的紫色圆点,有化龙点睛之妙,使得人人一眼就知这玉镯十分名贵。
可是惜桐却吓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上世戴在手上的玉镯,竟然在这世出现了?!
“怎还不上来?让阿玛替你戴上。这是阿玛今天在皇宫里得到的赏赐,你实在唱得太好了,所以阿玛把它赏给你!”
额娘把她往前推,她让阿玛拉起她僵硬的手,套上玉镯。玉镯太大了点,阿玛把它撸到她的手臂上。
“怎还在发呆?还不谢谢阿玛的赏赐?”大奶奶发话了。
她连忙跪下磕头:“谢……谢阿玛赏赐!”
阿玛又说了什么?她根本没听见,只像机械人一样被额娘牵回她们的座位。
她撸下玉镯,痴痴地瞪视着它;没错!这个玉镯就是她上世戴的!可……可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额娘叫了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说了一句:“额娘,我没事……”
她话还没说完,有一名侍女走到她们身边,在额娘耳旁说话;额娘脸色一变,又羞又怯地低头,指着她说:“那……我的女儿……”
“姨娘放心,等一下就会有人来带小姐回房,您不用担心。”侍女说。
侍女说完,脸色****地看一眼惜桐,就转身离去。
“额娘,她要做什么?”
“没……没什么,待会儿……会有人带你回我们的房里,额娘今晚……”她低着头说不下去了。
惜桐顿时明白:刚才的侍女是来通知额娘,今晚由她去侍阿玛的寝了。
她的计谋成功了!
可是她却高兴不起来,只因手上这枚玉镯出现得太离奇怪异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二百多年前?她没想到这只玉镯的历史竟然如此悠久!
少说有二三百年了吧?
她记得这只玉镯是她在七年前,也就是重生前二年的除夕夜得到它。
那一年的除夕夜,也和重生前的除夕一样,妹妹念桦和弟弟怀枫答应要回来和她吃年夜饭,只是她左等右等,等到九点钟他们还不回来,一气之下,她穿上外套到街上闲逛消气。
后来第二天醒来,她发现自己头痛欲裂,像是昨晚喝醉了一样,而且手上多出了这个玉镯;问了弟妹知不知道这个玉镯怎来的?他们都摇头说不知。
“老姊,昨晚看见你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时,手上就戴了这个玉镯。”弟弟说。
奇怪的是她并不记得自己喝了酒,但不管怎么说,这玉镯从此就戴在手上;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得到它的。没想到,居然会在这儿再次瞧见它,它到底是什么来历?皇帝赏给阿玛的,那表示它价值不菲啊!那又怎会流落到自己手上?
她就这样满腹心事地东猜西想这个玉镯的来历,直到寿宴结束。一名府上的仆妇向额娘福了一福,告退后牵着她的手把她送回小院落。
嬷嬷发现额娘被留下来侍寝时,高兴得抹泪,直嚷着老天有眼,终于让额娘一圆心愿。她在心里叹气;在这样的时代,女人最大的保障竟然是要靠男人的垂怜而活;她决不这样做,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不依赖男人的施舍。
嬷嬷把她送****,她也真累了,闭上眼就睡着。
这一睡,竟然做了个怪梦:
她满腹怨气地走在冷清的街道上,寒风习习。街上的行人莫不行色匆匆,看样子就知他们赶着要回温暖的家,和家人团圆。在这一年一度、全家团聚的节庆日子里,谁不愿意回家享受亲情的温暖呢?
她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足足走了二个小时,才渐渐气消,静下心来踽踽独行。这时已近深夜,四处冷清;街上行人几近绝迹,连向来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也只剩一两辆车子呼啸而过。
她信步走到街角,看到总是在那儿摆路边摊的老沈,那晚竟然也出来做生意。
“沈叔,今晚怎还出来摆摊子?没回家过年?除夕夜会有客人吗?”她走到摊前拉把铁圆櫈坐下。
“回哪家啊?老家早没人了,我孤家寡人一个,不出来摆摊做生意,还真不知要做什么好。再说,你不就是客人吗?告诉你,我今晚生意不差,这城市里像我们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呢!”老沈笑嘻嘻地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她自嘲地想,说得没错,她虽有二个弟妹,但简直和没有一样,她不是孤家寡人,是什么?
“来碗打卤面吧,顺道切点小菜。”她说,自己没心情独自吃那些年菜,现在也真饿了,不如给老沈做点生意吧。
“就来!”矮壮的老沈说着,开始忙碌。
这时她看见──在正播着春晚节目的小电视机后头,也就是面摊旁边,竟然还有人在摆地摊。她伸长脖子看:一盏小油灯旁,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板櫈上看书,而他面前的地上摆放一个架起的长箱子,里头尽是一些玉石。***
10 来历(二)
可在这昏黄的灯光下,那些玉石看起来不怎样;事实上她倒觉得那些玉石都像赝品,不是什么好东西。但那位老先生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长袍马褂,手里拿着一卷书,给人的感觉却如古画般,别有一番中国读书人的风范与气质;只差他花白的头上没有一条长辫子,不然活脱脱就像从清朝走来的古人一样。
这年头竟还有人穿长袍马褂?可能是应景吧?才把压箱货拿出来穿。
唉!会在这时候出来摆摊卖货的人,不都是一些孤家寡人吗?有家庭的人,谁会舍得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出来做生意?
这么一想,她不由得再仔细看那位老人家;他的脸上虽皱纹不少,但那文质彬彬的光华,还是由内而外透出来,让人心生亲近之意。想必这位老人家是位有学识之人,不是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吗?可怜这样的人,竟也沦落到在除夕夜摆摊做生意的田地。
“老伯,一起来喝杯小酒好不?我一个人喝太乏味了。”她出声招呼那位老先生。
老先生闻声,抬头看她,展现一个温煦的笑容后,拱手作揖说道:“不客气,姑娘……”
被婉拒了?看来这位老先生还颇有气节,不随便占人便宜。这么一想,她更坚持了:“您老别客气,大家都是有缘人,在这佳节不把酒言欢,好像对不起这节日的气氛,您说是吗?”
老先生想了一下,把手中的书放下,又作了个揖说:“那老朽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她连忙笑嘻嘻地拉开旁边的圆櫈,再向老沈说:“来瓶茅台吧,二个杯子。”
老先生撩起长袍下襬,气度万千地在圆板櫈坐下,又道了声谢。
“您别客气,今晚我们就权充是一家人吧,在这里畅饮、吃饭、看春晚,不也是其乐融融吗?您要不要在来碗面当夜宵?”她不敢问老先生是不是用过餐了,怕伤了人家的自尊,所以只说是夜宵。
老先生点头:“喝碗热汤也好。”
看来是没吃过饭,又不敢要求太多,便只说来碗汤就好。这老先生这么客气,反观家里那两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弟妹,她的心蓦地一疼,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