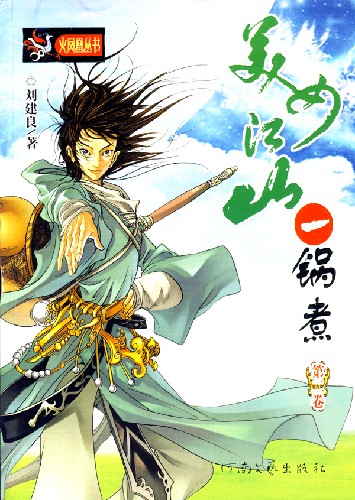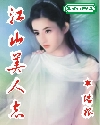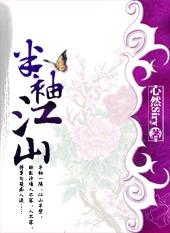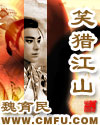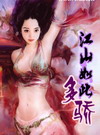江山多锦绣-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若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承启耸耸肩,脸上挂着一丝无谓的笑,“因为我也不愿意。”
“其实把清河嫁给你是两宫太后的意思。”笑容不减,承启继续道,“前阵子她们听了承康的游说,要我早日下旨玉成你和清河的美事,被我一直拖着。”
“你不愿意,是因为我的缘故,还是因为促成这件事的是承康?”无视承启话中的含义,王淳忽然开口问道。
承启愣了愣:“两者都有吧。”他想了想,又道,“我也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朝廷,本想替你直接拒了。只是忽又想到,清河确实温柔娴淑,男人娶到她真算得上有福气。何况我昨夜亲见你这里冷清寂寞,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若是你能与清河结为夫妇,子孙绵延……我倒不好凭着一己私心断了这桩婚事。”
王淳无奈的笑了一声。
“有个邺郡君做先例,还不够吗?”轻轻的揭起承启心中最深处的那块伤疤,王淳带着残忍的笑容继续道,“清河县主好歹也算得上是你的妹子,难道你想让她将来和邺郡君一样?”
“莞儿的事只是偶然……”承启的嘴唇蠕动着,“你和我不同,你必能待她好。我……唉!”他垂下头去,将脸深深的埋入凌乱的被褥中,“不要再提她了!你若不愿意娶清河,回绝了便是!”
“承启。”王淳将他的脸强行从被褥中拖出来,苦笑着看着面前这个永远自私自利的人,“你老实告诉我,我没有去上朝的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
“……”承启嘴唇动了动,却偏过脸,不肯正视王淳的眼睛。
“你突然来我这,就是为了对我讲要我娶清河的事吗?”王淳扳着他的下巴,将他的脸扭了过来,逼着他的目光和自己对视,“你有心事。”
“我甩开你的手,你居然没有给我一巴掌。而且,昨天夜里居然会屈尊降贵的到我这……我在你身边这些年,你何时想过踏进这里一步?”贴近承启的脸,王淳在他的耳边轻声询问,“说吧,是什么事让你转了性子?”
“说了又如何?”似是受不了他的亲昵一般,承启偏过头,“你不会答应。”
“你不说又怎么知道?”继续攻击着承启的脖颈,王淳的声音里有着鼓动和诱惑,“也许你说了,我就会答应。”狠狠咬了一口形状漂亮的锁骨,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痕迹,“不要忘了,你是我的皇帝。”
“你!”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人压在身下,他啃咬过的部位亦传来淡淡的疼痛与焚烧般的火热,承启不由气苦,嘴里说的好听,这人如今哪有半点身为臣子的模样?!
他试着推开王淳,却被人不耐烦的抓住双手狠狠别了过去。
“说吧,乖。”另一只手也开始不老实起来,带着浓浓的诱惑。
“贺兰人……派兵挑衅边境。”似是放弃了抵抗一般,承启软□体,像溺水的人一般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吞吞吐吐的说出这样几个字。
“嗯,然后呢?”身体被那人的手拂过便带起一片火热。而听到这样的消息,那人的声音居然也能如此平稳,似乎并没有令他感到如何震惊。
“十万重兵压境……朝中无将。”承启的目光中透着悲戚。该死的贺兰族居然趁着环庆兵变的时机想要浑水摸鱼,眼下外忧内患重兵压境,身为皇帝他原本应主持大局,可他却在与王淳发生御书房的争执后心慌意乱。回想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自己的手足无措,承启的心中不由一阵悲哀。
身上的人笑了起来。
“想让我去吗?”他俯□,轻轻亲吻着承启的眼睛、脸颊、嘴唇,像是在亲吻最珍视的宝物。被他如此温柔的对待着,承启不由轻轻点了点头。
“又怕我带兵远征不受朝廷控制,所以要我先娶清河?”
“是……”虽说这个顾虑最初由两宫太后提出,但承启自己心中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该怎么办好呢?”带着点困惑的口吻,王淳抬高身体,玩味的望着那双已经开始变得迷茫悲伤的眼睛,“如果是四五年前,我答应下来不会有半点犹豫。如今。”他低下头,碰碰承启的嘴唇,“你要给我什么?”
“你要什么?”在这种时候谈条件了吗?面对突然转变的王淳,承启更加难过。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要赐给他一些什么,却无一例外被拒绝,如今他却在这种时候开始提条件,难道连这个人也被那些蝇营狗苟的臣子们影响,学会趁火打劫了吗?
王淳笑了,他埋首于承启的颈肩,深深的叹了口气。
“我想要的你永远也给不了。”
承启看不到他的表情,却隐隐约约能猜到他未说出口的话。犹豫了一下,他小心翼翼的伸出手,环住王淳宽厚的肩。
“我们这个样子,不够吗?”咬了咬嘴唇,承启终于鼓起勇气一般开口,“我心甘情愿与你做这种事,不够吗?”
“你给我的只是一时一刻。”王淳亲吻着他的眼角眉梢,“不够,我想要一生一世……”
“太长了。”无奈的摇摇头,眼睛笼上一层雾气,承启苦笑着,“一时一刻已是奢求。”
初生的春笋被一层层剥去表层坚硬的外壳后,剩下的只有不设防的、柔嫩的笋心。只是那笋心也只可在每年的初春雨后才能寻觅得到,错过那最美好的时节便晚了,也迟了。
泪水不受控制的顺着承启的脸颊流了下来,沾湿了王淳的嘴角。
“你想要的,我记着便是。”
我也不愿你再背负着这天下,我只想要你属于我一个。承启不知道的是,剩下的半句话被王淳咽回了口中。
作者有话要说:病假了。T T
61、61。谁持白羽静风尘 。。。
永平六年,又是一年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牧童口里的歌谣伴着带着寒意的微风在已经可以窥到春色的田野间回响着,黑色的水牛悠闲的寻找着最嫩的青草,牧童在田间轻轻的甩着鞭子,为水牛赶走落在背上的牛虻,远处,勤快的农人已经抓紧时机春耕播种了。
三年前,西北边关的贺兰族趁着环庆兵变,朝中政局不稳的时机派兵挑衅边境,十万重兵压境,时局一下子便紧张起来,犹记得当年京师的大街小巷都在对边关的战情议论纷纷。驿道上,传递信息的信使在西北与京师间络绎不绝的穿梭着……但是终于胜了,虽说战争一打就是两年,虽说有大批的精壮男儿前仆后继去了边关,但好在战争终于胜了。
有的人回来了,带着大把的赏赐与妻儿团聚,有的人却将一缕英魂永远的留在了贺兰山。
“官家。”张公公轻轻的推开了御书房的门,跪在了地上。“轿子备好了,要移驾忠烈祠吗?”
“嗯。”房间内响起了沙沙的声音,是官家在收拾朝中公卿们递上来的奏折的声音。张公公连忙趋前几步,“这些事唤咱家做就好。”
“不妨事。”咳嗽了几声,承启笑着将书案整理好,视线落在了张公公身上,“礼部都准备妥了?”
“是……都妥了。”张公公毕恭毕敬的答道。忠烈祠是在本朝建立的,全为了纪念在贺兰山上战死的英魂。回想当年,为了是否应该建立忠烈祠供奉殉国将士,还曾引发了朝堂诸公的一场大辩论。
反对者的理由很明白,朝廷没有钱再去额外花费这样大的一笔费用。不仅仅要建祠堂,还要派专门的官员照管看护,保证在忠烈祠里供奉的香油长明灯永远长明……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一向那么介意朝廷财政的皇帝,在这件事上却异常坚决偏执。
忠烈祠就这么建起来了,礼部也调派了数名祭官昼夜照管。犹记得皇帝第一次驾到忠烈祠,那正在值守的两名祭官慌忙接驾行礼的时候,却被至高无上的天子止住了。
“这里供奉的是我永平朝的英烈。”两名祭官不敢抬头看向皇帝的脸,只听得他的声音温吞如水,“逝者为尊。你等既然在这里替朕供奉诸贤英灵,不必向任何人参拜。特别是在此殿上更是不可。你等可曾见过僧人在释迦牟尼面前向朕叩头吗?”
“这……”两名祭官一时语塞,却也不敢抗旨,只得畏畏缩缩的站起身来,不甚自然的行了礼,添了香油退下了。
忠烈祠内的祭官不向任何人行跪拜礼的规矩,便是那时候形成的。
原本定的规矩是每逢春郊、秋祀便由宰相代天子去忠烈祠行祭拜礼,但皇帝对忠烈祠却表现出莫大的兴趣。每逢初一十五,只要有片刻余暇就要去忠烈祠呆上半日,最开始出行的仪式极其隆重,后来便摒退了众人,只带上几名贴身侍卫、宦官随身保护。而且……常常在面对那些被祭祀的逝者牌位独自发呆。
这些并没有逃过张公公的眼睛,他也隐隐约约的能猜出为何,只是猜出归猜出,却不敢说也不敢劝。
忠烈祠建于京师的东南一隅,距离大相国寺并不遥远。这是一所典型的宫殿式建筑,大门正上方高悬一匾,写着“永平忠烈祠”五个大字,正是当今皇帝李承启的亲笔手书。
承启的车舆在忠烈祠正门前停住了,至高无上的天子走出车舆,望了望那高悬于正门、毫无生气的匾额,默不作声的步入了祠中正殿。
那一日,似乎也是清明。
信使的马蹄踩在朱雀大道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奔驰声。一身黑衣的信使骑在白色的骏马身上沿着御道疾驰入朱雀门,却例外的没有人上前拦阻,那使者一直冲进崇政殿前才翻身跃下马背,面容神情浑身上下都透着精神的气息,到得殿前,抬手递上折子与国书:“贺兰族发书于我朝,折冠求和!”
这个消息立时令朝堂上沸腾了,满朝皆喜。花白着胡子的宰执吕宗贤笑吟吟的几步上前,接过国书与折子,将它直接呈到承启面前,“大喜,大喜呵!”
平日里再如何告诫自己喜怒不应形于色,此时脸上也忍不住透出兴奋的潮红。
被这场战争一拖就是两年的永平朝再也不用源源不断的向前线输送军士、粮草、战马!负荷过重的财政终于可以偷偷松上一口气,派遣到前线的将士们也终于可以回来与家人团聚……而自己,也赢得了十几年的时间不必再担心贺兰族蠢蠢欲动的狼子野心。
从此尽是太平天下,万里江山,边疆再无战事!
带着愉悦的心情,接过吕宗贤手中递上来的奏折,迫不及待的翻开想要细读。所有的喜悦却在看到那一块羊脂白玉时消失殆尽。
似是要确认那枚小小的玉璧是不是残存的幻象,承启闭上眼,再睁开时白璧仍静静的躺在他的眼前。阳光从崇政殿的正门映了进来,映在白璧上,映出圆润的光和自己的影子。
全天下,恐怕再难找到一枚如它这般莹洁白润的玉璧。
承启的目光落在玉璧上,他情不自禁的伸手拿起它。触指是温润的冰凉,小小的玉璧上系着的红色丝线早已褪色,变成了黯淡的深棕。玉璧上刻着两个字,那两个字是什么,承启已经没有余力去看清了。
信使已经依礼站起身来,他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踏了一步。
承启勉强抬起头,正对上信使炯炯有神的目光,仿佛一眼便能看透他纷乱心绪的目光。承启顾不上去叱责他的殿前失礼,他的心此时已被迷惑和各种复杂的情绪塞满,一些情感在胸中不受控制的奔腾咆哮着,试图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勉强自己仔细打量着这位千里迢迢来送信的使者,眼前的人高大英武,一眼望上去便是将材的模样,兵部曾经报过他的名字和来历,说是王……说是那个人在贺兰山侧收编的某部族首领,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信使见皇帝的目光望向自己,轻轻点头行礼,身子却退到了一侧。
早朝在承启纷乱的心绪中匆匆结束了,众朝臣山呼万岁带着各种喜悦议论纷纷退去后,那名信使似乎知道皇帝仍有话要问他,脚步没有挪动半分。
移驾御书房。
面前只有信使一人,连亲信的太监都被摒退的时候,承启才肯慢慢打开折子。折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楷书,不过是捷报、军情而已,他定下心神仔细浏览那字里行间的文字,除了那个令他心惊肉跳的噩耗,再也找不出半点与那人有关的蛛丝马迹。
“你叫什么名字?”承启的目光终于落在不发一言的信使身上。
“下官雷逾渊,曾是羁縻州雷家堡堡主。”
“你从前方来,前方的战事想是清楚的,与朕讲讲罢。”
雷逾渊不着痕迹的望了他一眼,张开略显厚实的嘴唇,声音中听不出什么抑扬顿锉。
战事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派往贺兰山的那支军队唤作镇北军,朝廷为了慎重起见采用了吴均的建议,用老将周胜做主帅,王淳做为一名略有军功的翊卫郎只是那众多副将中不起眼的一个,主管襄办军务。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王淳将属于自己的公务做得尽心尽力,就连对他这种出身羽林军的新晋军官一向看不太上眼的镇北大将军周胜对王淳也是青眼有加。镇北军中,王淳保持了他沉默的本色,他很少开口干涉周胜的军务。无论周胜安排他做什么事,他都会完成得很到位。
战况从第一年的被动防守变成了第二年的主动进攻,面对着逐渐溃散的贺兰军队,所有人都乐观的认为将贺兰族远远的赶出永平朝的边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士气空前高涨,士兵们在训练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镇北军没有辜负朝廷赐给它的名号,很快,这支军队便可成为永平朝军事上一支有力的铁拳。
变化从镇北军的主帅周胜和襄办军务轻车都尉王淳之间一次小小的争执开始。
争执的原因并不复杂,在不断的胜利消息传回京师后,朝廷理所当然的下了一道圣旨。战争的目的,已经从最初的保家卫国变成了开疆拓土。
镇守和林的大将军郭英被调走,新的和林守将按照周胜的建议,任命为他的侄子周承。周承亦是将门之后,他早亡的父亲便是建宁朝都指挥使。有了父亲和攻无不克的叔叔做后盾,加上自己的骁勇善战,周承长大后在军中屡立战功。周胜推荐周承守和林,也并不是完全出于私心,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