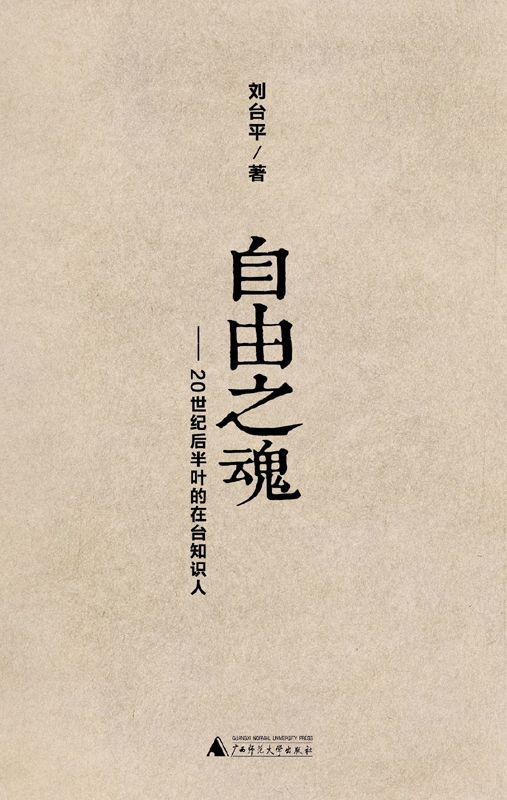重申自由主义-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一种特殊照顾是凭主观好恶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那些有凋萎之虞的目标,在道义上并不因此而降低其价值,反而可能更为有价值;二是那些对被忽视的目标十分珍视的人们,比起那些靠“市场的盲目任性”而得益的人们,也享有并不较小的权利,应该可以看到这些目标的实现。应该由一个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的国家来对双方都给予平等的机会;任何一个价值都应得到可能,可以同任何别的价值一样茁壮地盛开,必要时不惜采取实际上差别对待的办法,而且任何一个人都同任何别的人有同样的机会去成功地追求他偏爱的目标,而不问其追求的是怎么样的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不是不正当的)。对任何自称为艺术的产品,都不能以其丑恶、可憎或讨厌为由而拒绝它分享到一份公共资本;对任何人都不能因为所企图表现的东西是“反文化”的异端或是因为他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而把他定为被淘汰者、“怪物”、变态者从而加以排斥。
对于“百花”式的中立,只要稍为仔细观察一下就尽人皆知,这等于提出一些难以办到的、违反常理的要求。它规定对“任何”价值都给予“平等”的照顾,看来是禁止了有轻重高低之分。由于合情合理的价值的数量是无限多的,因此,对每一个价值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扶持,或甚至扶持到同等昌盛的地步(无论程度高低如何),都会像个无底洞似地吸收掉大量资财,除非给予每一个价值的资财是小到微不足道的。然而,“百花齐放”,乍一看来却是多元性的价值中立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更有甚者,这个解释具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针戏与诗”,对于政府以及对于那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对政府起出谋划策作用的人们,是要求他们作出相当严格的自我克制的。而另一方面,“百花齐放”则鼓励政治上的活跃,吸引尽量多的压力集团纷纷出台来要求支持,并且创造出一个让政府能同它所扶植的价值一道繁荣昌盛的气氛。无论这是值得欢迎的还是值得惋惜的,它仍然是符合现今已成为自由主义主流的那一套思想的。
这样,我们就发现,有两套有关价值中立的说法,代表了两条彼此对立的原则、两套根本对立的政策指导思想。历史上早先的“针戏与诗”论,要求“各人有各人的价值。”他要实现这个价值,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去实现好了,不能对别人施行强制,逼别人去帮他实现他的价值。“百花齐放”论则是较后才出现的,它主张“每个价值都有平等的机会”。既然没有市民社会,那就只能由国家来实行机会平等。
如果自由主义中真的能容得下这两个学说,那么,自由主义的确是多元性的。但是,这一来,它就难以继续自称具有面目鲜明的本色了。
二、目标与规则
现在回头来看,自由主义在其本色上遇到的麻烦,也许早在它的理论的深层逻辑结构上就已经伏下了一笔,这个结构对于自由主义的内容竟然变得众说纷纭是大有关系的。如同许多别的政治理论一样,自由主义的结构是由两个成份合成的:
(-)一个最大化公设:对于各种政治安排的评判,其依据是能期待这些安排对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有多大的帮助。这些安排,其目的就是要在尽可能大的限度内实现这个目标。举个例说,如果最大化目标(maximand)是国力,那么,相应的理论就会主张采取一些最适合于促进国防、投资、人口增长的政治安排,而同时抑制公民,不使之放纵。
(二)遵守一条规则(或一个规则系统)。政治安排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设计的,都必须依照这条规则办事。一条最根本的规则,就是政策必须符合该国的宪法(宪法的实质内容可以由一个辅助性的理论勾勒出来);或者是自然的正义必须得到申张;或是必须强制实行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平等关系。
总的说来,一个政治理论可以解释为在(一)与(二)二者都有其立足点。它的典型的设计就是要促进最大化目标,而同时又遵守规则。但是,二者通常在其各自的边缘发生冲突:越是严格遵守规则,目标的最大化就越是受到限制,反之亦然。(但是,现代的规则功利主义则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范例,认为它们的关系可以不是如此,或起码可以期待不是如此:规则要求遵守一套特定的道德诫命,而对规则的遵从,则正是为了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导向最大限度的功利。)
显然,优先通行权既可以给予最大化目标,也可以给予规则。如果最大化目标得到了优先权,那么,理论就是在事实上主张在规则留下的空间范围内实行“有限制的最大化”。举个例子来说明:(最大化)我们旨在达到我们所能达到的最快的经济增长,(十规则)这增长是同保持环境质量相容的。如果我们将优先次序颠倒一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类型的公式:(规则)人权不应受到侵犯,(十最大化)在不侵犯人权的前提下应以公共利益为优先。如果问什么为优先,或是问什么服从什么,这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那个诱导性的问题,问剪刀剪布时,究竟是两片刀片的哪一片把布剪了。
把优先地位给予目的或是给予规则,虽然这只是空中楼阁,但仍不失某种象征意义。它有助于为一个政治理论定下调子并制约它对语言的选择。所以,两个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有同样的结构,但一个号称以自由为导向(将自由最大化),而另一个则号称以权利为导向(制订一条规则,规定某一张单子上列举的种种自由必然得到尊重与推行)。前一种理论号称以自由为优先,后一种则号称以权利为优先,但这在实际上没多大关系,二者的主张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各自为其申辩理由时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
一个政治理论之对于一个政治群体,要么是对它加以说明,要么是对它加以规范。如果是对它加以说明,那么这个理论是用来理解已有的政治安排。如果这些安排是为一个最大化目标服务的话,这个最大化目标又是什么?——这些安排假定应该遵守的是什么规则?而另一个方面,理论在规范性方面的用途,却是推论出有哪些安排会最有利于在符合已选定的规则的情况下促进已选定的目标。自由主义也同其它政治理论一样,应该符合这些标准。然而,自由主义既能够赞扬某一特定的政治做法或体制,亦能对之加以谴责。其所以能如此含糊,原因就是在于它的那个“最大化加规则”框架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广义地说,它的最大化目标是自由,而它的规则是自由的行使可以因为要保护他人的利益而受到限制。
除了某些例外,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通常都使用一种相当笼统的、往往又是含糊不清的概念来表达自由,这个概念并不局限于那些旨在让个人能对集体决定施加影响的言论、集会与选举自由。但是,自由这个概念可塑性是十分大的。种种可以往这个概念中塞进去的含义简直是无限多的。以保护利益为正当理由,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而这些利益,同样也是包罗万象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释。对于自由以及自由所不应跨越的利益,人们所能采取的态度,归根到底只能是主观的、“无法证明的”,以内在的无法赢得的、有争议然而又驳不倒的论据为依据。在松散的范围内,可以将杂七杂八的内容塞进自由里去,几乎任何利益都可以自称为某一不可侵犯的权利的充分理由。
可以论证,自由主义的范围如此广阔,这恰恰是它之所以日渐丧失其鲜明面目与严格内容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 自由
一、“我行我素”
我们不妨不嫌赘叙,回过头来想一下,为什么自由本身不能独自作为目标,为什么它必须受到一套合适的规则的约束。事实上,这些规则的性质如何,是政治理论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我们读到一段有关俄国农民的描述,他肯定不是被过多自由所惯坏了的:
他最朝思暮想的,就是能够完全地、不负责任地自由。对于这个理想状态,他用的词就是volia,这个词指的是‘我行我素’。能够volia,就意味着可以放纵:可以狂欢,可以痛饮,可以把东西烧掉……。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曾一针见血地说:
我们的老百姓把自由理解为volia,而vodia又意味着我行我素。俄罗斯一旦解放,它不会走向议会制,而会走向酒铺,喝烈性酒,甩玻璃杯,把刮胡子并穿礼服大衣的贵族吊死……
如果自由的最大化,其赤裸裸的意义就是人人都我行我素,那么,一望而知,负责将自由最大化的权威当局就不会对每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包括胡闹在内)施加任何限制了。按照虽然有点靠不住但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二分法,这意味着任何人的“负面自由”就尽可能要多大就多大。反之,如果将正面自由最大化,就会使本来很少的作出(非琐事性的)选择(包括胡闹)的机会加大,大到物质上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供焚烧的干草堆越多,就意味着正面的自由越大。
显然,这些含义是不能接受的。即使加上一个对平等加以规定的分配性短语,对这些含义加以修饰,也无济于事。研究自由的哲学家,尤其是康德和斯宾塞,都曾使用过样的规定,来照顾别人可能因某一个人的自由而受到影响的自由。有影响的美国自由主义者约翰·罗尔斯也对每个人自由的平等采用冗长的、画蛇添足的强调词语来表达他的最大化原则: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可以分享广泛而全面的一套平等基本自由的体系,这体系是同人人均有自由的类似体系相容的。
把有着重点的词语索性都删去,这句话的意思仍是不损分毫的。既然人人都有权分享同一套体系,权利也就当然是享有该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而既然每个人都享有同一套体系,那么,按定义来说,这些自由当然也就必须能同一切人都分享这一点相容了。
然则,对于平等的这种画蛇添足式的强调,实际上并没有使得那使自由最大化的原则稍微更能站得住脚。因为除非“一个自由的体系”得到十分小心细致的界定,否则它在人与人当中的平等分配仍然不能提供保护,使得每个人不受他人自由的损害;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种损害甚至可能比分配不平等时更为广泛。因为如果某甲有焚烧干草堆的自由,某乙就应该“平等地”有焚烧干草堆的自由,包括焚烧某甲的干草堆。二人都享有尽可能大的“负面”自由,不受政府干预,不受法规阻碍。他们的“正面”自由,由于可以问津现有的一切干草堆而最大化了。不幸的是,互相损害他人的利益,就使得他们那种同任何他人的自由处于“平等”地位的自由所给予他们的满足感荡然无存了。
一个人的自由,除了在口头闲谈之外,能否被说成是同另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因为到底二人的自由是否有共同的定量特征,足以衡量比较,这是极为不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撇开不论,从volia一例可以得出的教训就是:将自由最大化,成为无限制的自由选择,是可以迅速导致荒谬的结论的。因此,如何定下一些限制性的规则,使自由免于陷入荒谬之中,这个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强制与任意
在“我行我素”原则之下,一切都端赖那条限制性的规则来制止最大化,使之不能胡来。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严酷的原则,使得应受限制的自由变得更为驯服。
哈耶克曾经提出过两条原则,都是有关某些人可能被称为的“负面”自由的。
(一)“无强制”就等于“我行我素”。最低限度的强制意味着自由在某种正当的、不荒诞的意义上已经被最大化了。要将这个意义是什么弄清楚,对强制的理解也应该清楚。
如果采取某一行动或威胁要采取某一行动,以图将他人的种种抉择的价值(代价)加以劣化,劣化到足以强迫他非作出某些抉择不可或强迫他不能作出某些别的抉择,并且使受强制者因已经对威胁屈服才在精神上得释重负。那么,这种行动一望而知是不正当的,是一种侵权行为。
但是,任何同意有国家存在的政治理论都给国家保留了施行强制的职能,这种强制,由于某种理由,不是不正当的,而是合情合理的。任何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松散的或是严格的,都很关心去探索国家的强制究竟超过了哪个限度就不再是合情合理的。在古典式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以及不那么鲜明地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一个自由主义政体的政治纲领,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将这些限制加以收紧与严格化并使国家受其制约。(在意志自由论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当然没有什么合情合理的强制可言,哪怕这种强制是多么微小。)无论限度放在什么地方,将强制最小化,一直缩小到这个限度,这对自由最大化原则并无任何种益(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是同义的),也提供不了一条限制性的规则来保护人们免受他人的自由选择所损害。
(二)“必要的强制”稍为贴题一些,因为它所指的是某一特定程度与方式的强制,这种强制既不是零,也不是仅仅“最低限度”,不像人们所追求的那种恰当的、使损害最小化的限度。这个强制放在什么地方是十分不清楚的。但据我们大家所知,它实际是可能高于现在实有的程度。在哈耶克看来,负责任的个人需要有一个保护框架,以便能按照自己的处事标准来过自己的生活,这个框架又需要有一整套法律来支撑,而所谓“必要的强制”,正是推行这一套法律所需的那种程度和那种类型的强制。而一般的法律体系,又是以道德原则为出发点的。同“最低限度必要的强制”相容的法律体系,其依据的道德原则是那些经过“自然淘汰选择”,亦即经过那些采用这些原则的社会所取得的较大成功而证明自己站得住脚的原则。
解释(二)比解释(一)更为接近于哈耶克的主张。乍一看来,它提供了一条本身就包含了自己必要的限制性规则的最大化原则。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