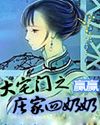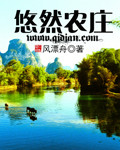中国在梁庄-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胡球拾俩粪也挣俩钱,现在是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反过来说,楼上楼下跟我支书也没关系,那人家都是出门打工。不出门打工,那还不中,在屋光守二亩田,吃饭都艰难。
说到自己的穷苦,清道哥显得很激动,父亲在一旁大笑说:“你娃子别能,说得你好像受屈了一样,你不当村支书,你能在公路边盖那一处房?你养活仨儿子,还办养鸡场?就别在这儿摆穷了!酒你没少喝,赌你也没少来,你输的钱都是哪来的?”清道哥是我们一个门上的,还没有出五服,平日里父亲和他对话都是连说带骂,毫不客气,见清道在我这里撇清,父亲早就按捺不住了。
这我也承认,是沾点光。不过,我干的时候,一般不去镇上食堂,减少开支,村里穷得不得了,你再胡吃,那还行?谁对口有啥事,哪一天哪一日为啥事,月底报销,一样样审核。不管在家里招待,还是在食堂,规定多少报多少,超一部分是自己的。我每天都记账,流水账。今天在干啥,跟谁在一块儿吃饭,都写得很清。
我当官的经验是,群众通情达理的多,不论理的也有,凡事有问题,首先从干部自身找问题,别先找老百姓。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通情达理,是你干部没说到。那年交公粮,有些群众拒交,我跟去三天,三天嗓子都说哑了。有些群众有怨言,借交粮可找着机会说说。能解决的我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给人家解释清楚。但是,交公粮是国家的事,该交粮交粮,随后再处理。借交粮胡闹,总归是不对。后来,村里人都说,早像你这样,俺们咋会不交粮?该解决解决,该说清说清,有啥说的?
现在的国家政策,对老百姓是够点'6'了。种地给钱,补七八十块钱,土地咋能荒?乡、村两级不向群众要钱,并且国家补贴,群众对上没有经济负担,收成好了多收点,不好了少收点。现在的村干部职责很简单,一是宣传党的政策,处理计划生育任务、宅基地、治安、民事纠纷;另外,村支部生办法引导群众致富,过去的干部逼着要钱,现在也变成服务型。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村支部帮助把事办了。
有人说现在的农村新政策,根本不需要村干部,干脆取消算了。这绝对行不通,就现实来说还是不适宜,如果那样,农村的老百姓就真成了一盘散沙。政府与农村肯定有间隔,具体的农村纠纷上面政府解决不了,一是不了解情况,村里的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谁家跟谁家有啥来龙去脉,外人一点都不了解,很难处理;二是真假难判,乡政府不可能直接进入农村。把这层取消了,下面的群众不成集体了。村里精简人可以,但机构不能取消,等于断线了。一个村千百户,政府直接工作到户是不可能的,上面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
咱们这任县委书记,我是真佩服。第一次开三级干部会,我听罢之后说,妥了,咱们县有指望了。干的都是实事。人家开会,会场掉个针都能听见,台上台下,鸦雀无声,理论联系实际,土洋结合,深入浅出。说个笑话,别的书记开会只想睡觉,都是套话,没意思,人家开会连解手都不愿去,怕有些话没听见。
我熬了五任县委书记,都没人家的水平。新官上任,不办事可有差,没考虑成熟,一办就岔气,劳了民又伤了财。过去各任领导都要搞项目,那年种苹果,公路两旁挖得像战壕一样,结果一个苹果也没有。还有“书记工程”,各乡都在自己的地上圈个院子,搞项目,脑子一热,不根据实际情况,强压硬办,逞能的浪费百十万,窝囊的浪费几十万,最后长的全是荒草。
现在,搞杨树经济,我觉得可靠。领导开群众动员会。我说,个人感受,两句话:有脑子种上几亩杨,十年之后强似小油坊。过去领导都搞特色,最后都劳民伤财,一穷二白。我种十五亩杨树,一年一棵树能长一寸,就长八寸粗,几丈高,就按四百块钱一方,一棵树半方,两百块,一亩地五十四颗杨树,那有多少,你们自己算了。比你养儿强,你就是养个好儿,他能给你回报多少?孙儿往家一留,年下回来,给你三五百元,你喜得不得了。不回来一个电话可把你老汉打发了。回来了不是想他爹想他妈,主要是娃子留在家。手里没有一分钱,孙儿都不往你身边跑。手里攥有四五万块钱,也够你养老了,不找娃儿们麻烦。现在废地种几颗杨树,你老了也安排好了。这个项目,我支持,绿色银行。
国家政策变了之后,最起码不存在荒芜土地。有本事在外打工致富,没能力在家种地也不受作难。总的来说,国家政策好,给农民带来好处,给村干部也带来好处,干群关系也好了,除了给村里办好事,不用登门要钱。这个政策过去从来没有过,开天辟地。现在纠纷也少了。
国家只要强大,这政策就会长远。好的政策,群众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有凝聚力,说明国家越来越强大。现在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好处,国家号召了啥东西,老百姓也愿意支持。
肯定也存在问题,再好的社会、再完美的政策也有问题。那远程教育好是好,给你个电视机,往大队部一扔,算是回了老家。就是你办,也没人去看。岁数大的在家种地,看孙娃儿,忙得头都抬不起来。不出差子'7'还怪好,一出事就完了,爷奶承担不了。你五奶奶现在一提起她那孙子,还是哭。娃子们都是爷爷奶奶看,留守儿童,管不住,没有几个想上学的。村里人精神涣散,死气沉沉的,现在村里死人,得找两个队,抬棺人才能找齐。这都是问题。
但是,都不急,国家也得慢慢来,恁大个家,也不是一天两天转过来的。
其实,在梁庄,清道哥并没有很强的根基,他父亲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上过台面。上任支书梁兴隆下台后,村里族人不愿意梁兴隆的儿子再当支书,硬把清道哥弄上台,谁也不得罪,谁也没话说。上台之后,清道哥显示出自己的从政才能,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挺好,对父亲和老贵叔这样的“老刺头”尊敬有加,时不时请他们吃个饭,商量点事儿,把几个老头儿哄得晕头转向。把兴隆儿子安排成村长,又把老保管的儿子任命为治安主任,也算让他们“世袭”了。清道哥在说到这个词时,很得意。村里普通群众虽然有意见,但是,因为这利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不知道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因此,虽然私下里议论议论,但因为清道哥的“清廉”,大家也没什么大动作。
几十年来,国家对乡村的政策一直在调整,中间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现在,政府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从表面上看,国家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减轻了,但是,却也遮蔽了许多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民主程序、村民自治虽然已经喊了三十年,但是,对于一个内陆的小村庄来说,它们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词,政治、权利、民主等词语距离农民还是很遥远。国家、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根本性的互动,一种建立在理解、尊重、平等基础上的互动。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是民主政治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家庭的主要成员长年不在家,对村庄、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至于土地,它不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再是“命根子”,无论政府怎么折腾,无非就是要税或不要税,多要税或是少要税,不足以形成一种巨大的牵制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基本的行政单位,村庄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项目,也没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任村支书:让谁干这活就是让谁累死
本来和村里现任支书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来一月有余,却一直没碰上面,问起老支书,老支书只摇头,说过去的村支书天天在村里转,现在的村支书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儿转,反正是上面,不会朝下面看一眼。这天,到乡里了解一些情况,中午吃饭说起这件事,乡党委书记说马上安排见面。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村支书正在镇上喝酒,据说是调解村里的宅基地纠纷,花了很大工夫才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块儿,他这个中间人不能走,否则,事情就又得从头开始。乡党委书记并不生气,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等了约有一个小时左右,我们的村支书韩治景进来了,略有点醉意,看见乡党委书记在,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一看便知关系非常好。看见我,很惊讶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连连说:“从你哥那儿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还说啥时候一块儿吃饭呢。”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形,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接任村支书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购粮食生意,现在也兼营修路、修桥,有搅拌机多台,主要用于出租。
其实说这些,估计你也大致知道。不说大的行政村,光说咱们梁庄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块儿,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户,人均不到一亩地。经济方面,主要靠外出务工。啥企业?有俩私人砖厂,从挖土烧砖变成石灰砖。韩家云龙有个养猪场,前几年养背时了。这几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猪投保险,保险六十块,个人拿三十块,政府拿三十块,最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千把块。户下散养的有四十多头。都是喂饲料,喂草太慢。没有闲人去割草。为啥养猪少?一家完全投入养猪划不来,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尽管有补助,还是养的少。
咱们现在不是杨树经济吗?村里河滩地种有六七百亩,我也种五六十亩,最粗已经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树投资得二百五十块,我觉得收入与种庄稼一样,只不过是最后弄个总疙瘩。十年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能卖三十万块。把投资去掉,能挣十万块钱。也就是个定期存款,有个养老钱。
现在种地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就这,种地的人还是少,农村劳力已经习惯出去挣钱,很难回来。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补贴钱,是好事,但不会形成你说的返乡潮,那点钱够啥用,想盖房子、孩子交学费,还得靠出门打工。但也有新变化,就是原先让给别人的地又都要回来了,种些简单的农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钱交粮,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
咱们这儿的人还是没那个生意头脑。挣了钱回来,存在银行里,等着有一天盖房子,只怕钱没了。银行存款很多,盖个闲房子,没人住,又扔那儿不管了。南方产品丰富,市场发达,家家户户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组织做生意。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打工挣点钱,商量着做个啥事,赔了算了。咱这儿根本不行。人心不齐,还没干出名堂呢就闹意见,凡是几家合伙的,开始可好,称兄道弟,到最后没有不结仇的。也有攒了不少钱的,不愿再出门,想着干个啥,可东看西看,下不了决心,怕赔,最后,还是出去了。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干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当干部的人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离多远,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的、有威望的去说合,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新的规划很难实行。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得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