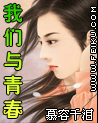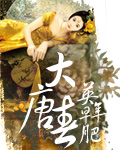一池春-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三儿,你也跟了本官这么多年了,今次脑子叫驴踢了?”张显阳啧的咂舌,手上的如意也不转了,直勾勾的盯着刘三儿,“用不着近身盯着,他们不是住了酒楼,没去驿馆吗?我也不用你一直盯,三天,这三天之内,他们必会登我巡抚衙门的大门。但是我要知道,这三天中,他们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听明白了?”
刘三儿面上没什么表情变化,可是鬓边盗出的汗珠,却出卖了他。
张显阳只当没看见,又点了点桌案:“另一宗事,着手去办吧,要不动声色,知道吗?你可别辜负了本官这么些年,对你的栽培。”
刘三儿弯了腰说是,一一应下来,垂下头时,眼神略变了一回,可是等到再抬起头来,却又一切如常了。
……
卫箴他们是把酒楼包了下来的,给的银子多,掌柜的看了满心欢喜,同先前住下来的客人一一赔了不是,又拿着卫箴他们给的银子,悉数赔给了人家,总算是把人全都给撵了出去。
这样的举动,其实已然有些大张旗鼓了,但谢池春和吴赞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是等着张显阳先找上门来的。
圣旨他们有,张显阳这个巡抚也一定早就接到了密旨,只等着他们这些上差抵达福州,便开始着手查办汪易昌通倭一案,是以作为不敢明目张胆的告发汪易昌的张显阳来讲,必然算着日子,见天儿的安排人在城门守着才对。
如今他们进了城,张显阳就该避开耳目,先找上他们。
张显阳的态度,其实也很关键。
案子是得这么查的,并不是说你张显阳先告了状,就一定得听你的。
这一路走来,先后又出了杨明礼的事儿,更让此案显得扑朔迷离,卫箴便更加不会轻易就信了张显阳的那些话,还有他所谓的铁证如山。
倘或真是铁证如山,为什么不敢明着告御状?当初他要是把手上的证据一并送往京城,内阁也好早做决断,是抓是杀,内阁议了,再回给陛下,也就是了,哪里有这么麻烦的事情?
是怕汪易昌反了吗?他不过握着福建一省的军权而已,就算通了倭寇,也难敌天下兵马。
这其中,只怕另有猫腻。
况且郑扬当日往福建送信,杨明礼却久久没有动作,仿佛压根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一样。
如果郑扬这个徒弟跟杨明礼的事情真没关系,那杨明礼的案子,跟汪易昌,关系也就不会太大,可路上又突然冒出这样一件事,保不齐是想要祸水东引。
可引的究竟是谁身上的祸,还得两说。
一直到这日临近黄昏时分,郑扬带着个人,敲开了卫箴的房门。
郑扬进了门才发现,吴赞他们都在,于是眼神变了变,合着说得好听,什么一起查案,真遇上要商量事儿,还是把他排挤在一边儿。。。
他面色不善,迈过门槛儿,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径直往旁边儿坐过去,冷哼着白了卫箴一眼:“你不是有很多事情想问吗?人给你带来了,要问什么你只管问。”
卫箴这时看过去,跟着郑扬进门的人,带着个黑色的兜帽,把整个人都罩了进去。
他眉头微一拢:“你这样子过来……”
来人把兜帽摘下来,露出来的是一张圆润的娃娃脸,白白净净的,倒生的可爱。
他请了个安见过礼:“卫大人不必忧心,福建的事儿,师傅大概其也跟我说过,真惊扰了人,才更好,卫大人不动,我不动,他们都不动,这案子,还怎么查呢?福建的水浑了,可都浑浊在底下,明面儿上还是一片清澈,非得搅动起来,你才看得见,哪里是浑浊的,哪里是干净的。”
谢池春听来,心道怪不得当年能做郑扬的左膀右臂,这样子口齿伶俐,条理清晰,的确是个能干大事儿的。
卫箴便果真没多说什么,也不与他绕弯子瞎扯,扬了声一针见血的问他:“汪易昌真的通了倭?”
他没说话,眼中却闪过惊诧,大概也是没想到,卫箴还真的这样直截了当,于是先是侧目看向了郑扬。
郑扬欸了声:“看我干什么?我不跟你说了,卫大人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招儿,你可别藏着瞒着,叫我知道了,头一个不纵着你。”
蒋招立时正经起来,又打个礼说徒弟知道了,跟着才转回目光,落在卫箴的身上:“大人久居京城,我却是长住在福州府的。要是说汪指挥使通了倭,您可着整个沿海这一带去打听,看百姓不把说这话的人舌头给拔了。”
很得民心啊?
卫箴搓着手指想了想,没言声,拿眼神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第一百零八章:一言难尽的征兵令()
第一百零八章一言难尽的征兵令
横竖话也都说出口了,蒋招大概是也没了什么顾忌,更何况郑扬还坐在这儿,他说这些话,那是郑扬点了头的。
之前郑扬来信诘问他,为什么汪易昌通倭的事情,他没能上报朝廷,反倒叫张显阳抢了先,难道他身在军中,身为福建的守备太监,却这样子玩忽职守吗?
那时他也慌了。。。
汪易昌通倭?这怎么可能呢!
再者说了,他们这样的人,外放做了守备太监,那就是陛下的眼、陛下的耳,他凡事不敢不尽心,更不敢有一刻懈怠的,唯恐叫人家拿住把柄,那就是万劫不复,还要连累了他师傅。
“沿海这一带,这些年倭寇越发的猖獗,谁拿他们有法子?”蒋招掐了掐左手虎口处,显然是气不过的模样,“后来他们都怕了,老百姓怕,当官儿的也怕,不要说我们福建省,卫大人您尽管往浙江、广州去打听,要不是朝廷把灭倭的旨意逼到他们脸上,他们谁敢去招惹倭寇?”
卫箴倒听明白了,不阴不阳的哦了一嗓子:“汪易昌却敢,是吗?”
他这话语气古怪的很,蒋招眼神略变了变,又很恭敬的同他做个礼:“您大概要以为,汪指挥使是拿着这个当借口,暗地里却行的是通倭的事儿。您容我说句不该说的,打从我认在师傅跟前儿那天起,就再也没有服气过谁,昔年在宫中时,就是司礼监的大太监们,我见了,也绝不卑躬屈膝,更不会佩服半个字。”
他一面说,一面站起身,眉眼间早就没了笑意,脸色凝重又难看:“卫大人大概觉得我轻狂,可话便是这么个话,您心里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不是要在您面前摆谱儿说嘴,实则是后来外派到了福建来,打心眼儿里佩服敬重这位都指挥使。”
太监们嘴里没几句真话,但郑扬是那个例外,他大多时候不屑于扯谎,除了是必要的时候,比如说,在如今的昭德宫面前。
蒋招其实骨子里有些像他,早年又跟在他手底下,是他手把手调教出来的。
当初蒋招没外派福建省,卫箴对他的行事做派也是有所耳闻。
司礼监的人个个眼高于顶,在内廷中,又有谁敢顶撞忤逆他们一句呢?可蒋招就敢。
这样的人,能对汪易昌打心眼里钦佩,足可见汪易昌其人绝不是那样的大奸大恶之辈。
他久不做声,郑扬坐在旁边儿挪了挪,扬声又叫招儿,跟着问蒋招:“张显阳上折子说他通倭,你回信说一言难尽,这又是怎么回事?通了就是通了,没通就是没通,哪里有什么一言难尽的?”
蒋招便回了句您容禀,把身子稍稍转一转,偏头看向郑扬的方向去:“一言难尽的,不在于汪指挥使,而在这位巡抚大人。”
卫箴听来,立时拧了眉:“张显阳?”
他又说是:“这话得从半年前说起。半年前巡抚大人下了一道征兵令,不只是福州府,福建省下的各府各县,凡年龄在十六到二十五的青年男子,不管成家与否,只要不是残疾,身体健康的,全都要拉来充军,对外说的,是用以剿灭倭寇。”
卫箴当下同郑扬对视一眼,两个人显然都大感意外。
谢池春朱唇微启,眼角眉梢也是难掩惊诧:“征兵是朝廷每年有定例的,除非是战火纷纭之时,不然不会轻易下什么征兵令,即便是权重如一省巡抚,也没这个权力。福建省的倭乱已非一日之祸,朝廷多少年也没特意再加征兵力。”
“所以汪指挥使当时就不乐意了。”蒋招掖着手,对插在袖管里,站在那里没动,只是眼风斜着扫过了谢池春一回,话仍旧是对着卫箴说的,“卫大人大概知道,征兵这种事情,本就不是归巡抚衙门管的,就算是真的要灭倭,兵马不足,那也该汪指挥使下一道手书。而张巡抚一道大令下来,老百姓怨声载道,骂的却不是巡抚衙门。后来也陆陆续续的抓回来好些壮丁,要调教、要归整,全都是指挥使的事儿,弄到了校场去,又全都成了大麻烦,不禁不服管教练不好,反倒弄得军中人心不安。”
他说着稍顿了下,须臾又低声叹息一回:“要换了是我,也心下难安的。本来有倭寇为乱,我当个兵就已经够提心吊胆的,指不定哪日就没了性命,好在是一直没有什么风吹草动,才能勉强过日子,加上指挥使又严厉的很,谁敢鼓吹的军心不稳,立时就军法处置了。可现在倒好了,军中没消息,巡抚衙门却征兵,说要打倭寇,叫我这个当兵的怎么想?这不是要拿我的命去博吗?”
卫箴眯了眯眼:“在福建当了这么些年兵,总不至于……”
“您想说,总不至于连这点子事儿都经不住。”蒋招失笑着摇头,“可是大人,那是人命啊。这世上,有谁是真正不怕死的?真到了要真刀真枪的拿全部兵力去打倭寇的时候,你不怕吗?或许卫大人英武不怕,可您不能叫所有人都像您、像汪指挥使一样,总有人是会怕会退缩的。闹到最后,一传十、十传百,偏偏汪指挥使还没法子拉了人军法处置。本来人家就是寻常老百姓,不情不愿被巡抚大人抓来充军的,才进了军中,什么都没做,还要叫军法处置发落了,人家更要指着指挥使的鼻子骂。军心已经不稳了,要是民心也不稳,那不是叫倭寇有机可趁吗?”
谢池春却听出不对劲儿来,叫了声蒋公公:“先前不是说,汪指挥使很的民心吗?”
“那也只是先前呐。打半年前出了这档子事,多少人明里暗里的骂汪指挥使。”蒋招连连摇头,后来好不容易收住了,眼底的不落忍却没来得及收回去,“老百姓不知道,我叫人去打听过,都是说汪指挥使借职权之便,向朝廷请旨征兵,为的是要朝廷加派军饷和军粮,但最后还是喂饱了他自己而已。一群愚民,越传越厉害,说的煞有其事的,所以汪指挥使才左右为难。”
第一百零九章:是谁通倭()
第一百零九章是谁通倭
“这话不对。”吴赞眉头舒展不开,眸色写满了沉思二字,“平头百姓就懂这个了?这话是怎么散播起来的,就没人追查过?”。。
“汪指挥使是武将,没有那么多的文臣心思,他埋头干他的事儿,打好他的仗,练好他的兵,又怎么回去跟百姓计较这些?”蒋招说起这个也是无奈至极,“我不止一次去劝过他,也该好好的跟百姓们解释一番,他又不听,说是多此一举,说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先前替老百姓做了那么多的事儿,就是再狼心狗肺的,也没有为这个,就把他从前做的全都不认了的。”
是,这便是武人心思。
这份儿心思太简单了,实际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
人家都说,最可畏还是众口铄金,虽说天下悠悠之口难堵,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任由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时间久了,不是真的,也说成是真的了。
这个道理,汪易昌显然不懂,蒋招有心提醒他,他却还是不当一回事。
“那后来呢?”卫箴点点扶手,“他也没去找过张显阳?”
“找过。”蒋招的眼神变了变,提起张显阳,他显然充满了不屑和恼怒,“大概是在事发后的半个月吧,老百姓的口诛笔伐他不当回事,但军心不稳,汪指挥使就绝对坐不住了。我记得那时候他把征回来的兵,全都放回了原籍,还每人都发了半贯钱。把人送走了之后,他可能是咽不下这口气,而且舍出去的这笔钱,本来是不需要花的,现在却全都加在了军中开销,我也是后来问他,他才跟我说,当时去找巡抚大人,也有一部分用意,是要钱的。”
厉霄听来觉得好笑,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路子?
说他心思简单,可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怎么不骂到张显阳脸上?
照理说来,他跟张显阳这个一省巡抚也是平起平坐,谁也辖不住谁,但他怕什么?躲什么?张显阳莫名其妙干这种事,坏了他的名声,还搅的他军中不稳,连民间都怨声载道,他去不理会张显阳的胡闹?
到最后镇不住了,把人放回去了,为了这些钱,找到巡抚衙门去的?
于是他噗嗤一声笑出来:“这位都指挥使,也不知是个什么路子上来的,办的这算什么事儿?”
蒋招一眼横过去,显然不悦:“千户大人别说嘴,汪指挥使就是野路子上来的,也叫倭寇们闻名变色。”
他怕是真拿汪易昌当个人物,正应了他那句打心眼儿里钦佩,谁也说不得,谁也碰不得的。
厉霄想变脸,但话是他先说的没错,况且卫箴也瞪了他一眼,分明是叫他闭嘴别胡说八道,是以他只能讪讪的嗤了一回,丢给蒋招个白眼,什么话都不说了。
“你后来去找汪易昌,大概是什么时候?”郑扬脸色已经十分难看了,蒋招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他明显是很不满的,“最早出事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京城?我向陛下举荐你到福建来,你一天到晚都在操心什么呢?张显阳擅权僭越,巡抚大令一下,你就该把他参到京中,再不济,也该派人来告诉我一声,何至于把事情闹大,闹的都指挥使同巡抚翻了脸?”
蒋招的气焰立马就弱下去:“起初是真的没想到,况且军中情形,也确实复杂。汪指挥使一直都有心灭倭,但福建一省的兵力又确实不够,他也给朝廷去过几次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