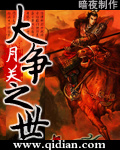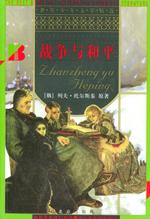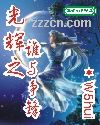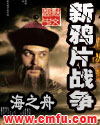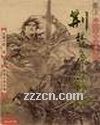尤对华战争-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着,由临时排防守的阵地被攻破,中国的火力转向旅部和后勤区。印度方面组织的反攻失败了。进行平射的印度野炮和坦克,堵住了中国部队;但下午四时左右,格巴兹·辛格下令部队向南方八英里左右的鲁巴(Rupa)撤退。他希望能在鲁巴同增援的两个营汇合;但当时一个营距鲁巴还很远,另一个营走的路线不同,开进邦迪拉时第四十八旅已经撤走。中国部队没有向他们开火,黄昏后格巴兹·辛格又返回邦迪拉,才把该营拉出来。
十八日夜间,该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但又接到第四军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Foothills)。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在鲁巴固守!这次,考尔又不在军部,而是跑到了伏特山,他是从该村派了一名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于是,部队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这时中国部队已占领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居高临下地对回来的印度人进行射击。这就使得鲁巴无法防守。全旅这时还保持为一个单位在战斗着,又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向查库(Chaku),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中国部队从山上跟踪追赶了一阵子,不时地袭击沿山路后撤的印度部队,后来就脱离接触。第四十八旅到这时只剩下了三个营的残部,加在一起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天,徒步后撤,傍晚过后抵达查库。先头部队事先已对该地作了侦察,并分配好各单位到达后应防守的阵地;这次撤退还算是有控制的。但午夜过后不久,中国部队从三个方面进攻查库,并伏击了一支向该地运送弹药给养的纵队。燃烧着的车辆照亮了防御工事,中国部队很快地就突破了印军阵地。全旅至此已失去控制,终于溃败,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三时左右,第四十八旅已瓦解。这时,在东北边境特区以及在西段中国方面所主张的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了。从军事上来说,中国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印度方面遭受到彻底的失败。
但撤退并没有终止。十一月十九日深夜,考尔回到了提斯浦尔军部,确信中国部队将进一步向平原地带推进。第二天早晨,考尔同森将军进行了会商,并当着森的面,下令要军部立即撤至高哈蒂(Gauhati),该地在提斯浦尔以西约一百英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当时K。K。辛格准将和其他几名参谋坚持认为他们应留在提斯浦尔,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经过一番争论,考尔也留下了,当天下午,军部的其他人员,除医院和伤病员等不能搬运的部分外,都前往高哈蒂。第二天,考尔搭乘直升飞机,飞过沿着小路溃向平原的第四师残存人员,并让帕塔尼亚和几名伤员搭上飞机回到提斯浦尔。
新德里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才发布瓦弄失陷的消息;事先还公布了关于瓦弄地区正在进行激战的报道。这个消息比塔格拉山脊溃败的震动更大。一般公众都认为,在塔格拉山脊印度部队是遭到了突然袭击,认为中国部队的进攻象是一次由步兵偷袭的珍珠港事件。但瓦弄却是一个重要据点,控制着通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通道,而印军在这里又足足准备了三个星期——事实上是采取着攻势——现在又败退下来。此外,当天晚上印度政府向报界介绍情况时,还宣布中国部队已进攻色拉,战斗仍在进行。第二天,人民院的议员们在整个提问题的时间里,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地坐在那里,到了中午,尼赫鲁站起来,宣布最新消息。
自上次议会休会后,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个期间大家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瓦弄大捷的消息。现在,总理不但证实了瓦弄已经失陷——当天早上各报已报道这个消息——还说色拉也失陷了。议员们鸦雀无声,屏息听完了尼赫鲁的简短发言。他刚一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了愤怒的质问和训斥,并发展成为一片鼓噪。议长要议员们遵守会场秩序,可是他的声音为一片呼喊声所压倒,根本无人理睬。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总理就会站立起来,用他那尖刻而又带讽刺味道的语调压住喧哗。他能比议长更有效地驾驭议会,因为他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处于这个全国危机的关头,很明显地需要议会表现镇定和克制的时刻,尼赫鲁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往日对于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想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尼赫鲁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但这也无助于恢复他的地位。在这已历时三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战争中,他讲话里时常出现的那种丘吉尔式的词藻,现在也消失了。这时,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乏,他讲的尽是泄气的话,而且使听的人也感到泄气。在这部不断扩大的灾难史中,他又增添了新的一项:就是邦迪拉的失陷。他的讲话还特别针对阿萨姆邦的人民,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非常伤心的。我很能理解我们在阿萨姆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切可以说都正在他们的大门口发生。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阿萨姆邦的人民对这番讲话的反映是辛酸的;他们觉得尼赫鲁是在伤心地同他们告别,预料他们不久将处于中国占领之下,并且默认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了。尼赫鲁接着说:“在侵略者撤出印度或被赶出印度之前,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多少是被一些挫折所吓倒了……”
关于这一天,就是十一月二十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
当天深夜,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他的想法是:如果中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就要美国飞机截击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部队;如果中国空军企图袭击印度的城市,就要美国飞机对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护。呼吁书提得很详细,甚至写明了所需要的空军中队的数字——十五个。这说明尼赫鲁是接受了某些军方人士的意见,但他事先既未同他的内阁同僚们商量,事后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份呼吁书唯一的一份副本保存在印度总理秘书处,而没有按照惯例送给外交部。
' 注:这件事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故的国大党议员苏迪尔·高希(Sudhir
Ghosh)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在尼赫鲁提出这项穷途末路的呼吁后不久,肯尼迪总统曾把这件事告诉了高希)。对此反应是强烈的,又是奇特的:人们指责高希污辱了这位不结盟之父的死后名声,而且是扯谎。当时的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把高希找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呼吁,在部里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载。高希要他同美国人查对,并说如果美国人否认这件事,他愿收回他的发言并道歉。以后去问美国大使馆,大使馆肯定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呼吁,并将呼吁书的原件出示给印度人(经过进一步搜寻,在总理秘书处的档案中找出了该件的一份副本)。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大使纪事》一书中描述过那份呼吁书的原件。以后的做法就是很不象样的了。夏斯特里在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词审慎的声明,这篇声明从字面上看是符合事实的,但从效果上看是骗人的。高希提到有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曾奉命开往孟加拉湾;夏斯特里否认尼赫鲁曾要求美国派一艘航空母舰,并说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开进孟加拉湾。高希表现出一种夏斯特里所不配的忠诚和庄严的风格,保持了缄默,虽然这样做使他自己的正直品格受到了损害,因为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知道:尼赫鲁在惊惶失措的时刻,已把不结盟忘得一干二净。但高希在他的自传里把事情的真相讲清了。甚至到了一九六五年,梅农也还不能相信尼赫鲁真的发出了上述呼吁。他说,“潘迪吉没有发出过那个呼吁”,“……潘迪吉在这点上是肯定的,不论他本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决不会干那样的事。”
' ' 译者注:潘迪吉Panditji,是对尼赫鲁的尊称,意为“有学问的长者”。 '
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太平洋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海面;但在尼赫鲁提出呼吁后二十四小时危机已经度过,因而那艘航空母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尼赫鲁还曾要求派遣运输机,美国立即答应了,就派遣了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上述呼吁还不是在溃败的震动下所采取而又很快翻悔了的唯一步骤。战争一开始尼赫鲁就竭力强调,印度只不过是同中国作战,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同共产主义作战;把二者区别开来,不但对于不结盟的姿态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必要的。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新德里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原来的意图是:只逮捕实际上已分裂出去的党的左翼成员,把那些不赞成该党领导承担义务支持印度政府的成员关进牢房。但内政部把事情搞乱了,他们从情报局的档案中抄下了一批要立即加以逮捕的名单,没有经过审查就发给各邦首府。结果,该党的许多中间派以及某些亲莫斯科派的成员都遭到逮捕。过后不久就发现这件事办错了;尼赫鲁向内政部长夏斯特里表示不满,并且说这样做会损害印度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誉。但如果打开牢门把他们统统放出去会使局面更加尴尬,因此决定把那些抓错了的人一个一个地放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人造成是承认错误的印象。
在内政部如此这般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操劳的同时,有些政客又在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担忧。一批反对党和国大党的议员找上了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建议他进行干预,施行某种形式的总统统治,暂时停止议会活动,把内阁变成为总统的谘询委员会,由尼赫鲁担任首席顾问。宪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条文。这项建议是昏头昏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几乎等于搞一次政变。它反映了这些人对尼赫鲁作为战时领袖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他们认为象拉达克里希南这样一个同导致灾难的政策没有任何联系的非政治人物是个非常时期的适当人选。总统对找上门来的议员们并没有给予任何鼓励,但由于某些被认为同他比较接近的政客(特别是蒂·塔·克里希纳马查里T。T。Krishnamachari)在首都把他们的想法广为传布,因此,总理就有了疑心,认为拉达克里希南对上述想法并不完全反对。
'
注:尼赫鲁对拉达克里希南原来是友好的;在这次事件后,尼赫鲁对他的态度显然冷淡,可能上述的猜疑是原因之一。另一因素可能是由于总统曾组织各邦首席部长共同施加压力来反对梅农。而且人们广泛地引用总统所讲过的话,就是说这次溃败是由于“我们的轻信和疏忽”,这点可能刺痛了尼赫鲁。
'
与此同时,在提斯浦尔人们害怕中国大举入侵印度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担心入侵者在几小时后就会到达。十一月十八日晨,考尔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他在电话中把局势描绘得那么危急,以致这位专员在接电话后很快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实际上这位专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正要办理移交手续,但当他听到考尔讲到无法抗拒的中国大军正朝着提斯浦尔方向席卷而来的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等候继任者的到来而推迟自己的行期了。)新的地区专员到达后,发现当地的民政机构已停止工作,市政当局曾通过扩音喇叭告诉市民说,当局已不能继续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有些当地的政客乘机活动,纠集了一伙群众对他们发表演说。
“'这些政客'由于感情冲动,把提斯浦尔描写成为印度国防的堡垒,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其撤走,莫如死于敌人的炸弹之下。这些政客又讲了许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却溜走了。提斯浦尔的市民也小心谨慎地效法他们。”大伙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的罪犯,拥挤在渡口,等候明轮汽船把他们渡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这只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三百到四百人,这时每次装载达一千人。有些没有走掉的人在国家银行里拨弄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细心搜寻。在此以前,银行的人员点了一把火企图把约三十万镑的现钱烧掉,其中包括硬币;他们原想把硬币都扔进一个湖里,但后来看到许多人都跳到湖里去捞硬币,他们才改变主意。当时,许多东北边境特区的晕头转向的部族人从一个方向涌进市镇,本市居民又从另一个方向蜂拥逃走,市内可能很快就发生抢劫和骚乱。但这时新的地区专员设法让一些粮店开了门,并开始重建秩序,有些陆军的工兵也采取了主动,接管了发电厂和其他重要公用事业。所幸当时在场的工兵部队不多,中央政府已派遣民防处长来到阿萨姆邦,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这位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Digboi)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当时还议论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如果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来干的话。
后来,人们把提斯浦尔所出现的混乱状态归罪于该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但至少一部分责任可以追到新德里的内政部所发出的指示,指示要求分清主次进行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