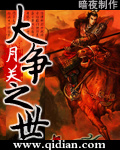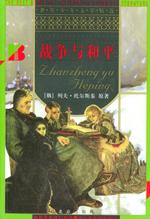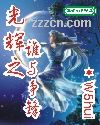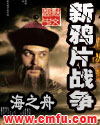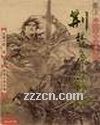尤对华战争-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印度军队“越境挑衅”是造成朗久武装冲突的原因。九月九日中国再次要求俄国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但当天晚上塔斯社还是发表了该声明。
从表面上看,塔斯社声明对谁都没有伤害。该声明说苏联“领导人”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对有人(指西方报刊)利用它离间两个亚洲大国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感到惋惜。苏联领导人相信,“两国政府会……解决所产生的误会”。
尽管这个声明讲的是一些陈腔滥调,但它却很重要。它受到普遍的欣赏,特别是在印度。尼赫鲁向人民院说,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比较不偏袒的观点”。北京的反应,虽然当时有所克制,但看来是强烈的。以后中国人说,莫斯科“摆出一付中立的面孔”,“不问是非曲直”,仅就朗久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这样俄国人就把共产主义世界的内部分歧宣扬出去。他们这样做是不听中国的劝告,对“中国关于事实真相所作的反复说明置若罔闻”,一心想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向美帝国主义献礼”。《人民日报》说,“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
十月,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从戴维营来到北京,北京领导人试图向他说明朗久事件的经过,指出地点是发生在实际控制线以北,挑衅来自印度方面。但据中国人讲,赫鲁晓夫根本“不愿意了解边界问题的真相,不愿意了解谁是挑衅者,一口咬定反正打死人就是错误的”。
在中印争执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使之感到烦恼和受到损害的双重困难。第一,中国人有个“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的问题。我用“信用差距”这个名词,并不是为了婉转地说中国人说谎,而是要说明人们面对着中印双方提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时,几乎普遍倾向于认为印度的说法是正确的。(不仅西方世界如此;世界上多数的共产党也都追随苏联之后接受了印度的说法。例如有一个与赫鲁晓夫同时在北京访问的波兰代表团在离开中国后曾对人表示过,中国是因为它自己被排斥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之外,才故意“向印度挑起”两次边界事件的。)第二,由于印度在大小战斗中都输得很惨,人们一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冲突不可能是由印度挑起的。
中俄两方在理论上的分歧的核心是:战争是不可避免呢,还是可以避免的?战争是能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还是由于核战争的危险而必需永远避免呢?因此双方在引经据典的争论中,也都以朗久冲突的含义来支持各自的立场。赫鲁晓夫在北京直接了当地反对以战争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他说:“不论共产党人的力量多么强大,都绝对不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使用武力。”中国认为这是对中国在朗久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又一次不指名的斥责。赫鲁晓夫回国后,向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报告中,仍然坚持他对中印争端的中立态度。他在听了北京的解释之后,明知中国对俄国所持中立态度是如何气愤,却仍然坚持其中立态度,这在中国看来无疑是蓄意挑衅和公然侮辱。
对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来讲,中苏分裂是一九六O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党代会上公开化的。中国处理同印度的争端,成为赫鲁晓夫所谴责的北京“左倾修正主义者”的中心内容。
赫鲁晓夫反驳了中国所提出的苏联不站在中国一边反对印度,就是对中国拆台的指责。他说,事实上是中国拆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台。中国同印度争吵,不仅是不同苏联合作鼓励印度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进行反对。当然尼赫鲁是资产阶级,但是中国同他的争论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纯粹是民族主义的争吵,这种争吵已经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说不尽的损害,更不用说使共产主义丧失喀拉拉邦那样具体的事情了。
' 注:赫鲁晓夫在这里把时间的先后搞错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是在边界争端具体化并成为政治方面的问题之前就被赶下台了。 '
在上述情况下,特别是在无法分清争端的是非的情况下,中国没有权利抱怨苏联不给予支持。他嘲笑说,中国夸耀自己人口众多,却还要苏联支持。而苏联人口还没有印度多。他提醒中国,应该牢记列宁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谴责,不要忘了列宁曾出于战术的考虑准备割让一些领土,而托洛斯基则曾加以反对。中国行动的结果是使尼赫鲁成为印度的民族英雄,这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苏联也有边境问题,但苏联对之采取了负责的态度;如果苏联也采取了同中国一样的做法,那它早就会多次向伊朗宣战了。在俄伊边界上曾发生过多次冲突,也有过伤亡,但是苏联不允许让这类事件引起战争,因为那样做是同革命的真正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赫鲁晓夫针对中国的立场,说明了俄国在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所持态度的理由。俄国的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始终一贯的。唯一的例外是在争端发展到高潮的边境战争中期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当时也正是古巴事件中俄美对抗期间。
' 注:见第四章第二节 '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所申述的立场完全同中国的立场一样。《真理报》写道: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相信中印之间没有理由发生边界纠纷……更没有理由使纠纷转化为武装冲突。……如果双方能坐到谈判桌上来,心平气和地、不带任何成见地讨论他们相互的指控,毫无疑问,冲突早就会得到解决。谈判即使再困难,也总比战争要好,争执的问题必须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而不能通过军事方式求得解决。
这番话同北京一再用来劝说印度的论据一模一样。北京要印度相信必须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公正的和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是容易取得的;任何一方试图用单方面行动实现自己的要求,必然会导致危险的和灾难性的对撞。
苏联竟向最坚决主张谈判的一方大讲其谈判的好处,这就说明俄国象西方的观察家一样,根本不相信中国在中印争端中和就该争端所说的话。他们似乎早已断定中国对边境情况的说法是一派谎言,断定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是虚伪的。由于北京同新德里的争论错综复杂,他们就不去进行客观的调查(赫鲁晓夫说过,“争端的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他们对尼赫鲁所表白的说他自己渴望谈判的表面那一套信以为真;他们不相信象印度这样一个弱国真的会在地面上向中国挑战。
' 注:见第四章所引苏共中央一九六O年二月六日通知。 '
鉴于尼赫鲁对苏联以及对中印争端所持的复杂态度,如果当时莫斯科对他施加影响,规劝他妥协或放弃前进政策,本来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苏联的明确中立态度却鼓励印度坚持自己对边境问题的立场,苏联的飞机更使印度得以推行前进政策。印度的朋友恰好帮助它走上了灾难的道路。
保持同印度的友好关系是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中心环节。苏联同中国的竞争和对中国恶感的增长,无疑地促使它站到印度一边。此外,中印和中苏边界问题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也很清楚地是决定俄国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的讲话含蓄地提到这点。他说,“苏联也有边境问题,但它对之采取了负责的态度。”赫鲁晓夫提到的虽然只是伊朗的边界,但他明白还有更大得多的边界问题,需要同中国解决。三年前,周恩来就曾想同他讨论这个问题。
中俄边界是帝俄扩张领土和十九世纪的中国衰弱的产物。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恢复了它在二百年前就已开始执行的向东扩张领土的政策,并吞了中国在黑龙江以北及其支流乌苏里江以东的所有领土,缩小了中华帝国的版图,割断了中国同日本海的联系。与此同时,俄国还从中亚细亚方面对中国进行蚕食,侵略中国土耳其斯坦(新疆)。在爱珲条约(一八五八年)和北京条约(一八六O年)中,中国承认丧失这几大片土地。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废除在多难之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收复它以前的边疆。
在革命初期,莫斯科洋溢着反映其革命纯洁性的天真烂漫的激情。布尔什维克党人当时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把沙皇遗留给他们的不义之物清除干净。一九一七年,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列·米·加拉罕(L。M。Karakhan)宣布苏维埃政府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九二O年的加拉罕宣言对上述声明又予以确认:
“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即使在当时,有的俄国人对他们的东部领地就持有不同看法。列宁说过,“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 '
译者注:列宁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谈到苏维埃共和国击退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匪并收复海参崴时讲这句话的:“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们大家都知道,内战拖了多么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海参崴的收复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胜利。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种众望把我们从内战时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也把我们从进攻我们的国外敌人手中拯救出来。这里我指的是日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5页)
'
此后不久,苏联就采取了这种观点:不管是不是不平等条约,中俄边界不能改变。他们以后又把加拉罕宣言曲解为只不过是作为谈判基础的基本纲要,而不是苏联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步骤的清单。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国民党人)继续主张加拉罕宣言上怎么说的就应该怎么做。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继承了旧日的争端和长期以来收复失地的要求。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苏边界问题,采取了与他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相同的态度。他们虽然同其他中国人一样,对不平等条约的非正义性以及不平等条约所象征的民族耻辱也深表痛恨,但是他们准备把已建立起来的边界当作生活的现实来看待,认为失地已不可复得。而且,从实际政治来考虑,必需采取上述方针。如果对一百年前已经丧失的领土依然坚持收复失地的要求,那就必然会使新的共产党中国同苏联进行一场无法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毫无希望的争执。很显然,不能指望俄国人会放弃包括诸如海参崴和伯力等城市在内的、为他们所长期占有并已开发了的土地。
中国把自己的态度清楚地告诉了俄国人:“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中国政府曾向莫斯科建议举行谈判以便解决边界问题。看来,当时他们没有料到谈判会有困难。当时有人向周恩来问到中苏边界问题,他回答说:“在地图上有很小一点点差别,很容易解决。”这当然是说得有点过份:中苏边界长达几千英里,原有的条约对边界的规定往往很模糊,它根据的是一些即使做了也是很粗略的勘察,但是双方如果有共同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无疑是能达成协议的。
一九六四年的中苏谈判几乎刚一开始就破裂了。苏联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场,正如俄国人自己事后所说的:他们坚持“边界全线都已由条约议定书和地图作出了清楚、精确的规定”,他们拒绝进行全面谈判。充其量,他们只准备“谈判在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
'
注:印度的措词与此惊人相似:“中印边界是一条以传统习惯为基础沿着自然地形的边界线,其大部分又由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印度'只准备讨论具体争议地点的边界位置,并在必要时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
'
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苏联既要占有条约规定它可以占有的领土,“又要中国承认它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俄国对谈判的态度等于是:“除了我们同意谈判的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这同印度的态度一样,同样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对这两场争端,中国的立场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中国从来没有象向印度正式明确保证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对苏联则明确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道理是很清楚的。不管条约是平等或不平等的,那些划定中苏边境的条约是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正式和合法的协定。但中印边境则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在麦克马洪同西藏人达成的协议中,中国并不是签约的一方,而且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该协议。中印边界的西段更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
俄国人可能把这些细微的区别看作只不过是中国人模棱两可的官腔,其目的是为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铺平道路。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致尼赫鲁的信(该信抄本第二天也交给了俄国人)中写道:“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