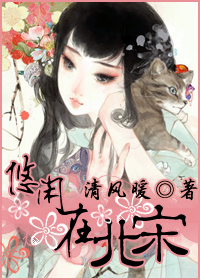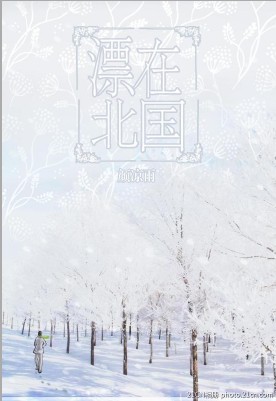一头大妞在北京-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班当过副带队,搞气氛比较在行。
后来就变成了我要是不在,他就会东看西看到处找我,宝气!
好在他是督导,不用到下面去卖东西,还能藏藏拙。他要是代表公司肯定让人笑掉大牙。可能因为他傻没人排挤,也可能他就是大奸若傻。直到我走,他还是在那个位置上挣着高薪,或许他可能得到了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真谛也说不准。
与他不同,我的顶头上司倒真是一个优秀的经理,当年一连拿下四所高校的全部业务一跃成为经理。年纪比我还小,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与业务员刻意保持着距离,这让我很不舒服。我不知在他面前表现成什么样子,更不习惯于像别人一样在他面前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大家不过都是打工的,你不过先入门做得好一点儿,并且你还吃着我们身上的提成,为什么我要向你低三下四,你愿意指导就指导几句,不愿意指导也没关系。何必把脸板得像夹紧的屁股一样,再说就他那年纪的小屁孩儿心里有多大事我还是知道的,就这样,我与他关系很远。
说起来也怪,他惟独对我还算客气。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也就是说我必须比别人做得好一些才能永保这份尊重和这个饭碗。
23
我运气还算不错,在这些新来的业务员中第一个拿到了单子,虽然是一个小单。那是我在学院路的一个高校拿下的。这个学校在搞五十年校庆,从上面批下来十几个亿,正不知怎么花。各路人马全部跑去为它出谋划策,大家都想分上一杯羹,工程承包商、系统集成商、还有我们这种靠教育吃饭的公司,一窝蜂地跑过去,那阵子在那个办公楼大家经常能打上几个照面。
这些高校的领导是一群败家子,大建特建各种门面工程,拿纳税人的钱不当回事。这很好理解,没有工程怎么花钱?不花钱怎么提钱?于是,就见这个学校到处都在施工,到处都在折腾,好好的柏油路被挖开,再重新建一个同以前一模一样的柏油路。这个学校的图书馆大约重新装修了两年,现在都不能正常开馆,门面倒是耳目一新,搞得很现代,惟一的用处就是供大家照相留念。
这个学校的这笔业务拉得还算顺利。我先是在电话里谈了几次,对方很牛,说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立项。妈的,十几个亿的资金就不能给学生多建几个多媒体教室?我才不信呢,不让建创造条件也能建。找了一天专门跑过去看看,管这事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干干瘦瘦的,口气很无礼。说现在有很多家公司在找他,一边说一边玩着手里的一堆名片。我看了看,旁边还有别的人,就例行公事地介绍了我们的公司,在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我看见旁边的人在接电话,正是好时机,赶紧甩出一句“我们公司各方面政策都很灵活”的话。他眼帘低垂,看来是听进去这句话了,这就够了,该说的都说了。
走的时候我管他要了张名片,他拿出一张名片,然后用笔写上了他的手机号码。
出门的时候很高兴,给了手机号这事就好办多了。
给大屁股脸经理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说想请这个人喝喝茶,能不能算业务招待费。经理同意了。我又问了一下回扣最高能给多少,大部分公司对刚到的业务员不会交待回扣的实底,这得你自己问,自己留心,能争取的政策一定要自己争取。
打完电话后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觉得这个单子应该能拉来。
24
周末的下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曲扬与林元都出去跑场子了。忽然看见邻居卖菜大嫂向我走来,低声急说:“快躲,查暂住证的来了。”
神情真是可怕,这个大院外来人口多,在当地很出名,所以,经常有人来查暂住证。但也许是稽查队,因为并不穿警服。
这个大院里的人做小买卖的居多,都舍不得钱办暂住证。我倒不是舍不得,就是不知如何去办,问了一下,说是先要工作单位盖章,然后再到四季青派出所。这是什么规定?那些没找到工作的人呢,难道你不让他住吗?后来的后来我又听说没有单位盖章也行,只要房东给你房产证的复印件,也可到居委会去办。这哪儿跟哪儿呀!谁定的这乱七八糟的规定?我同房东一说,房东根本就不同意,说这片我熟,你要有事直接喊我,我没喊过他,因为后来我越长越胖,不像坏人,走在街上,警察弟弟从来就没查过我。
那时我还没有办证,因为我来京总共也没多久。之前听过的传说已经很可怕,说是查出没证的人就要被抓到北沙滩筛沙子等,就像当年在深圳没有暂住证要被送到樟木头一样,估计是外地人听起来最恐惧的事了。
我慌得不知怎么办,怕死了,怕死了,我没干什么作奸犯科的事,但谁能保证不被抓到北沙滩呢?我抬头看去,有三四个男的正向这院里走来,他们直奔我左手边的屋。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抬腿就跑。正在晾的衣服也不要了,脚上还穿着大红的毛拖鞋,一口气跑到颐和园门口,头都不敢回。
颐和园门口有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因为天冷了起来,并没什么生意。
我看着那个卖东西的大姐,脸很善不像坏人,跑过去同她说:“大姐,我害怕呀,刚才院里有人查暂住证,你帮我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追来,我不敢回头,有人追来就说我是你老妹,才来北京。”
大姐笑了,可能她是听出我的口音了,红黑的脸膛上,白牙一闪:“哪有什么人呀?别自己吓自己了。”我也听出了她的乡音。旁边一个卖盒饭的中年男人,一口京片子正正经经地说:“别怕,人民警察是保护咱们的。”
我瞅了他好几眼,确认他不是在同我开玩笑,他大概把我当成山里来的无知少女了。
过了好久我才敢回头,自己的小屋现在肯定是不能回了,难说他们现在就在我屋呢,或者他们看到那个丢弃的洗衣盆,正在想像一个女盲流仓皇逃跑时的模样。
我给曲扬打了一个电话,曲扬说:“你还是先买双鞋吧。”好在口袋里还有点儿钱,我从大姐那儿买了一双那种老年人穿的黑帮棉鞋,十七块钱,这种质量很差的棉鞋是专门卖给外地来颐和园的游人的。
那天,手里拎着自己的毛拖鞋,穿着老太太棉鞋,一个人在外面逛了好久才回去。
到现在我也没办暂住证,倒是做了一个假学生证(有学生证就不用暂住证),中国政法大学的,北京假学生证一般都是假冒北大和中国政法这两所学校的,这两个学校倒了霉,每到春运高潮,时不时地就有一个民工说自己是中国政法的学生。只要三十块钱,比办暂住证便宜得多。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清河的家里有人来查,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说自己是成教的。他们看了看我满屋子里的书,很相信地走了。
25
周一上班的时候,我约了那个高校管事的出去喝茶,就在知春路的“晴耕雨读”。我喜欢这个名字,好听,有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北京人讲究这些,还有一个楼盘叫“锦秋知春”,也起得非常漂亮。就凭这名字,得争来多少客人呀!
到了那个地方,闲聊了一会儿,告诉他我们公司对优秀客户有出去旅游的奖励。可以去香港、新马泰,或韩日,对有重大贡献的客户还可以到欧洲。
这就是瞎说,刚开始大家不熟悉,不好直接谈钱。用一个别的堂而皇之的好处引诱更能消除隔膜,也显得公司背景很厚,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门面。
我大致说了一下,如何才算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客户,比如对公司市场的支持力度,有没有市场培养前景。这些都是废话,可是又是不能少的废话,最后才告诉他这些奖励大概相当于多少的回扣点。
他一直在听,黑瘦的脸上没有表情,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他慢条斯理地说,他大概只有一栋教学楼,只有六个左右阶梯教室要上多媒体,可能离优秀客户的要求相差太远。我算了一下,也不错,总比没有强。
我赶紧告诉他我会为他在公司尽量争取优秀客户名额。如果他不方便旅游,也可把这项费用换成现金发给他。
这种说法,一般人都能接受并且也愿意接受,钱总比不能预测的旅游来得实际。只可惜他不是一个大客户,他要是还有潜力,我还会用送红股诱惑他,虽然最后都要变成钱兑现。可是这么绕了一下,不就比直接给钱来得更容易接受吗?
人呀,真是很奇怪的动物。谁能把直接的买卖关系变成各种各样的互惠互利关系,而又显得温情脉脉、冠冕堂皇,谁就是所谓世俗成功的人呀。比如说老客户,比如说老领导,比如说是老情人,比如说夫妻。
单子最后成了,回款的时候是我送的信封。接过信封,他的脸依然很平静。
出门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这就算是来京后第一个小捷吧。
26
工作上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人却越来越感到寂寞、难受。颐和园那儿比较偏僻,到了晚上同农村没什么区别。刚来的时候是秋天,现在树叶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黑咕隆咚的夜晚,显得格外漫长。
颐和园门口总是有两个人守门,冬季根本就没什么游客,这两个人就显得分外的多余。也许是领导要求,他们每天像酒楼的迎宾小姐一样,天天站在那,神情凝重,目视前方,像两个多余的门神,又可笑又可怜。
每天上班时看见他们,不禁从心底升出一种怜悯。从他们的长相上看很明显就是北京人。这些北京人一般都做着如开公交车、商场售货等体力工作。
我来到北京最不明白的就是这件事儿,我除了在这种场合能看到北京人,偌大的北京我就很少能碰到北京人了。北京人都上哪儿去了?
如果推断得没错,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分人神通广大,在高处生活,不是我这个阶级所能接触到的;一部分人出去了,北京人不都是在纽约嘛;一部分人在家等着吃房租,啥也不想干,其实也是啥也干不了;剩下的没有法力也没有文凭的就是我所能见到的这些底层的北京人了。
也就是说整个北京轰轰隆隆的全是我们这批外地人与底层市民在拼命地忙着。何勇的《钟鼓楼》里说: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的烟
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他们的脸色也像我一样……
我就是一个辛勤的外地老乡,我天天夹个包,跑来跑去为了生计。但这在报纸上可能被称为“全民建设北京”,要是《满汉全席》里的那个四川妇女看见我,她一定会说:“大妞同志,建设国家?”
27
在这样的冬天我感到彻头彻尾的孤独。我是这样的年轻,正是怒放的季节,却在这偏僻的颐和园里无人理会。
本来以为到了北京,这个所谓的文化城,朋友一定不会少,来了才发现,我这样的处境能交到朋友真是难上加难。周围是一大群的人,能说上话的却没几个。曲扬与林元倒是好朋友,但那也是因为我对他俩的美貌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喜欢这两个漂亮朋友,至于所谓思想灵魂之类的沟通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明白我在想什么。
收支平衡才是不久以前的事,衣服基本都没买,穿的都是以前的旧东西。不会舍得钱去什么酒吧歌厅消费,更别提有时间看什么高雅演出了,基本就没什么娱乐活动。到京之后,生活质量很明显地下降了一个档次,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
我需要温暖,需要交流,需要有一个话语圈的朋友说说话。我需要干净的厕所,而不是天天戴上墨镜鼓起勇气冲向公厕,或者在夜深人静时,跑到颐和园边上的荒林里丢野屎。我更需要爱情,需要一个像样的男人像样地爱我一次。我需要拥抱,需要亲吻,需要男的大块肌肉压在我身上,然后在我耳旁轻声地叹息。
这些要求多吗?这不过都是些正常的要求,可是这些想起来好像就是天上的月亮,离我那么遥远。这样的生活让我很自卑,毫无乐趣可言。如果再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好久没有同男人做过了,甚至都忘了做是怎么回事。脸上的雀斑很明显,用一个朋友的解释就是“骚斑”,就是女人长期没人干,发骚时长的斑。她当时说的是她自己,被男友甩掉之后,她已经三年没有性生活了,满脸是雀斑。
我可不想变成她那样,我决定有机会一定要找一个“祛斑霜”。
27
快下雪的一天,我出去买东西,在巴沟村的长椅上见到两个小孩,一个三四岁,一个两岁左右,都是男孩,一瞅就是来京农民的孩子,脸蛋皴红,旁边放着几包方便面。
很多农村孩子的零食就是方便面。我特别讨厌这样的农村父母,不行就别生,生了就别让孩子遭这份罪。方便面能有什么营养?并且还是那种杂牌的方便面。阜阳农村大头婴儿的事多多少少也要怨他们父母贪便宜。没钱就别生孩子,自己都是这个社会的奴隶了,被命运摆布得像牲口一样,还要生出那么多小奴隶。这两个孩子一瞅就是哥俩,天,生活都那样了,他们的父母还要生。阜阳,那地方的特产就是光屁股娃,据说每到下雨天一个泥坑里站着一个光屁股娃玩。农村每家人家有三四个娃正常得就像天上下雨,那能不穷吗?于是就有贫穷、愚昧、贪污、官本位,于是就有上访和《中国农民调查》。
等我一个小时回来之后,发现这俩孩子还坐在长椅上吃他们的方便面,旁边没有大人,我觉得这事有点儿不对。这么冷的天,小孩子的脸都冻红了。我走上去问话,小孩子太小,话还说不明白。
“妈妈呢?”
“妈妈买东西去了。”
“妈妈去了多久了?”
“·#¥*¥#*”(方言,听不懂)
“你们什么时候来这的?”
“早上。”这么冷的天,早上就来了,到现在还在等妈妈,这事绝对不对。
“爸爸打妈妈了。”哥哥好像知道我想听什么,说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