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李逢吉和令狐楚想内外维持来牵制他的政治态势洞若观火,也在寻找机会来攻击两个人。第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了。长期战争带来的疲弊逐渐显示出来,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在延英会议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认为,罢兵的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理由劝宪宗放弃战争。这时,裴度保持了沉默。他知道,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那人,只能是他。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裴度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
几年来,宪宗见惯了官僚们喋喋不休的争吵、懦弱无能的姿态和让人伤心的推诿。裴度主动请缨的壮举让他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宪宗立刻让长于骈文的令狐楚起草制书,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就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心情沮丧的令狐楚很快就草草起稿,拟出了制书。这样的文字当然不能让裴度满意。他提请宪宗对制书中的三数句话加以修改。裴度就是故意要用这种出格的做法来表示他的不满。他相信,在这个紧要关头,正希望自己效命沙场、力挽时局的宪宗不会为这样的细节斥责自己,损害即将出征的统帅的权威。宪宗皇帝对裴度的用意也是心领神会的,立刻将令狐楚逐出翰林学士院。同时,李逢吉也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宪宗以霹雳手段为裴度扫清了后顾之忧。就这样,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裴度和他所代表的用兵之策,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反对者的名单:韦贯之、张弘靖、白居易、段文昌、萧俛、令狐楚、钱徽、独孤朗、张仲方……但是,他们并不都是朋党。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裴度和他对成德的征讨。李逢吉以为,他可以混迹这个庞大的阵营,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可是他错了。他没有看清,武力削藩是元和朝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宪宗皇帝不可违背的意志。任何阻拦的行为,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选择反削藩之策作为突破口,绝对是一个错误。
李逢吉落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操切。在宪宗皇帝态度暧昧,甚至还倾向于裴度的时候,他贸然在御前发言,暴露了自己支持令狐楚、反对伐蔡的真实嘴脸。当然,这也和他还不善于经营朋党有关系。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段文昌在这个事件中保持中立,显然是隔岸观火。李逢吉和令狐楚的谪贬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几年后段文昌稳稳地自翰林学士入相,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颠峰。
可见,元和晚期的李逢吉在政治上还稍嫌稚嫩,一帆风顺的仕途经历使他对权术的运用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元和宫变的发生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在政坛上异军突起,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贞元七年进士党的形势急转直下。皇甫镈、令狐楚相继被贬后,形影相吊的萧俛也很难在长安立足了。
与萧俛政见相近的段文昌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段文昌属于某一朋党。他的岳父武元衡是强硬的削藩派,可段文昌本人却持相反立场,和萧俛共同推动“销兵”,试图以平和方式解决藩镇问题。在李逢吉的提携下,段文昌步步高升,在元和后期顺利地进入了翰林院。可他没有贸然卷入李逢吉与裴度的争斗中去,和贞元七年进士党也没有太多瓜葛。在皇甫镈失势后,段文昌作为一个几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选,和萧俛一起拜相。这样一个立场中立的人物亟亟地想逃离长安的是非旋涡。他利用独对的机会,向李宥推荐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和元稹,为自己妥善地安排下一条后路。
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想染指宰相高位。这恰恰给了段文昌和萧俛交卸相权的机会。段文昌想和王播换个位置,积极地支持王播入相,好空出成都的位置。萧俛的态度和段文昌正好相反。他多次在延英会议上极力地反对对王播的任命。
作为贞元十年的进士,王播科名稍晚于萧俛,也是贤良方正科制举及第。早年时,王播的官声很好:补盩至尉的时候剖断狱讼明察秋毫,深得御史中丞李汶的赏识,被推荐任监察御史;在新的位置上,王播不畏权贵,冒着丢官的危险弹劾了污吏云阳丞源咸季,擢升为侍御史;贞元未年,王播因得罪臭名昭著的京兆尹李实被贬为三原令。在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顺宗皇帝即位后,王播迁驾部员外郎,擢任工部郎中、知御史杂事,每到一处都做得有声有色;王播任长安县令时关中饥荒,赈灾恤贫,深得民心。此后,王播扶摇直上,迁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元和六年起又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在新的位置上,他也显示出在财赋方面的过人天赋,确保朝廷对淮西用兵四年而“兵得无乏”。但是,元和十三年,王播受宰相皇甫镈的排挤,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的盐铁转运使也由程异继任。这次贬谪成了王播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播不见了,代之以一个搜刮地方、逢迎权贵、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播。
萧俛站在王播的对立面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廉的萧俛不齿于王播用金珠货币贿赂中人以求宰相的无耻行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播与皇甫镈久有宿怨,作为皇甫镈同党的萧俛不能不有所顾虑。尽管萧俛不惜以去留相争。但是,在贞元七年进士党失势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长庆元年二月,段文昌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王播虽然没有立刻拜相,但被留在长安,暂时担任刑部尚书,并再一次兼任盐铁转运使这一掌握财权的要职。谁都看得出来,王播入相只是迟早的事了。心知大势已去的萧俛对长安已经无可留恋,坚决地辞去宰相之位。
就这样,煊赫一时的贞元七年进士党彻底地退出了政治核心圈。
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持科举考试的钱徽推荐了杨浑之。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另一人选。但钱徽没有买他们的帐。
浑之不中选。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段文昌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和李绅的态度完全一致。
前面说过,中书舍人李宗闵曾经在元和三年科举考试的对策中抨击过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这一次,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金榜题名,把李宗闵也卷入到这一不名誉的事件中来。李德裕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元稹的崛起与段文昌在皇帝面前秘密推荐有很大的关系。但这只是他支持段文昌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也想借此机会打击李宗闵。十几年前的李宗闵与元稹是一对密友。但现在他们都是宰相位置的有力竞争者。围绕官位展开的明争暗斗使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元稹要借贡举案狠狠地打击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宗闵。
主持子亭复试的王起和白居易也各有立场。白居易曾与钱徽友谊笃厚。他们曾同在翰林学士院豹值,诗歌唱和,在围绕是否讨伐成德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他们的立场也是一致的。另外,白居易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都是参与舞弊的举子。所以,白居易偏向被告的可能性很大。子亭复试的另一位考官王起是王播的弟弟。既然段文昌正在积极地为王播争取宰相位置,王起投桃报李,支持原告也在意料之中。
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提起这一重公案的李绅是李党中坚,他背后似乎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存在。但由此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却证据不足。因为,与李绅并肩的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牛党领袖李宗闵和通常被看作李党成员或同情者的裴度、郑覃都赫然在列。所以,将长庆贡举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时,但钱徽不听。他最终被谪为江州刺史。李宗闵、杨汝士也被贬官。
翰林三俊在长庆贡举案中占尽了上风的。
我们知道,翰林三俊能在长庆初年迅速上升为长安重要的政治势力,是离不开李宥的赏识的。他们正是凭借着天子近臣的身份,在朝政上拥有绝大的发言权。论和李宥的私人关系,李逢吉比起翰林三俊并不逊色。元和七年,他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李宥还是皇子的时候,李逢吉就曾是他的老师。天子门生,成了李逢吉东山再起的资本。但是,李宥最初似乎没有考虑起用自己的老师,只是让他担任兵部尚书。在唐朝,六部权归侍郎。与宰相同为三品的尚书更多的时候和仆射一样,是留给前宰相们的荣誉头衔。但是,李逢吉不甘心以前宰相的身份安享尊荣。他悄悄地为自己重掌大权进行谋划。这时候,摆在李逢吉权力之路上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夙敌裴度;另外一个就是近来风头正劲的翰林三俊。李逢吉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暂时还很难撼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他来说,在一场鹬蚌相争中扮演渔翁的角色更为合适。
长庆贡举案中,裴度和翰林三俊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裴度之子裴譔因为翰林三俊的指控,失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功名。尽管李宥看在裴度的面上,仍然赐给他进士及第。但这丝毫改变不了裴度父子的尴尬处境。双方的矛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迅速表面化。此时的裴度正在河北征讨王庭凑、朱克融。他上表李宥,极力指责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在长安朋比为奸,对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贬魏弘简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表面上看,裴度占了上风。但是,旁观的人都清楚,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李宥很不高兴。考虑到裴度是朝廷中威望很高的大臣,又正在用兵,不得不作出让步。李宥感到自己被裴度政治讹诈了。元和十三年,裴度也曾用同样的手段来讹诈过宪宗皇帝。但是宪宗没有理会他。本性懦弱的李宥无法象父亲那样采取强硬的立场,也不可能。因为元和十三年没有战争。可现在,河北复叛的战火正在蔓延。李宥不得不向裴度屈服。
在这一回较量中,元稹失去了重要的职位,而裴度失去的是李宥的赏识。
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但仍然和过去一样,受到宠信。不久就在李宥的安排下成了宰相。紧接着,于方事件爆发了。
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宠骤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典型的弄臣。他急于用一件不世奇功来洗刷自己的负面形象。当于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向元稹推荐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于方告诉元稹,两人曾游历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以用反间计救出被叛军王廷凑、硃克融连兵围困在深州的牛元翼。这个大胆的计划打动了元稹。如果事情按于方的设计顺利进行,就能用两个人来做到裴度领兵十万都没有能做到事情。这个美妙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元稹。他立刻同意了于方的建议,赂兵、吏部令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实施反间计的时候给赐有关人等。李逢吉知道,他终于等来了他苦苦等待的机会。在他的指使下,同党出面向与魏弘简关系不睦的神策军左军中尉马进潭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一个叫李赏的人偷偷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行刺的对象就是裴度。虽然史书上只说李赏是因为元稹与裴度有矛盾,才对裴度这么说的。可我相信,李赏的背后是李逢吉。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谋深算的裴度隐忍不发。紧接着,李逢吉的同党站出来指控元稹行刺裴度。这不会是巧合。
最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在元稹贿赂兵部、吏部出二十通告身的时候,引起了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逢吉注意。只要他指示经办的官吏利用出告身的程序稍加盘问,是不难了解到事情真相的。在获悉元稹和于方的计划后,李逢吉首先指示李赏向裴度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元稹结交江湖人物是针对裴度的。他相信,裴度一定会堕入彀中。因为元、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相对处于下风的元稹有作案的动机。同时曾经在元和十年遇刺而大难不死的裴度对行刺是非常敏感的。一时冲动之下,裴度会全力搏击元稹,形成新一轮倾轧。
可是,李逢吉低估了裴度。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裴度选择了沉默。在深加戒备的同时,他宁愿静观事态的发展。李逢吉当然知道所谓行刺裴度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等待对他来说,等同于错失良机。在裴度迟迟没有动作的情况下,李逢吉只好让自己的同党告发元稹,主动掀起案件。
照我看来,裴度未必就不知道侠客不是针对自己的。但是,能把自己的政敌元稹置于被告席上,未尝不是他乐意看到的。所以,我们揣测,裴度即使没有以受害者的有利身份极力攻击元稹,至少也放任李逢吉一党诬告元稹。在他看来,如果元稹被扳倒,那自己的一颗眼中钉就被拔除了;就是不成功,至少也于己无害。可惜,裴度漏算了一着。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天子李宥。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李宥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立逢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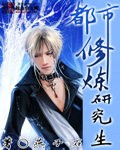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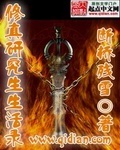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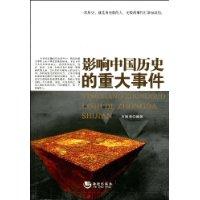
![(历史同人)[快穿]后妃记事簿封面](http://www.667zw.com/cover/13/1388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