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后双方就很默契地转入相持;被征召的藩镇是很乐意在前线安享朝廷供养的——平时他们的给养由自己领有的州郡提供;无法将优势转化为胜势的朝廷承受不了长时间消耗带来的沉重财政压力,不得不重新考虑妥协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军队因缺乏协调而遭到几次让人心惊肉跳的打击后,朝廷更是坚定地谋求体面解决危机;谈判条件会因事而异,但对朝廷来说都是失败……相同的情节一遍又一遍地上演。每一回,朝廷都廷饱蘸着淋漓的墨汁试图去书写不一样的历史,落笔却总是发现不出窠臼。重建集权中央的决心就在了无新意的重复中消磨殆尽。
但是,现在李炎决心偏劳李德裕的枢笔来作一篇大文章。李德裕也确有能力让藩镇题目在其手中翻出别样的新意来。
会昌元年九月癸巳,卢龙节度使史元忠死于兵变。这给了李德裕初次发挥的机会:他没有急于将节钺颁给暂时的胜利者,而是耐心地作壁上观,静侯更合适的人物和更合适的时机。如其所料,幽州局势风云姽谲,叛乱者很快死于新的叛乱。朝廷战略性拖延不仅避免了短时间内连续变更任命的尴尬,而且使藩镇的将领们认识到:没有中央的正式任命,他们的统治将因缺乏合法基础而处在高度不稳定状态。对朝廷态度恭顺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最终控制了幽州,顺利地得到了长安的认可。作为回报,张仲武和他统治下的卢龙相当长时间里在灭回鹘、灭佛等诸多问题上给予长安弥足珍贵的支持。其实,李德裕的策略与李绛对魏博镇之所为如出一辙,效果也仿佛。三十多年前,魏博归服是元和中兴的关键。没有田弘正效命,宪宗在河北藩镇问题上取得任何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李德裕通过完美的政治操作,为朝廷赢得了元和七年曾有过的契机。因此,当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亡故的时候,朝廷可以更从容地应对这一人事变动了。刘稹一厢情愿地希望能效法河北旧事,世袭叔父的遗缺。但朝廷断然拒绝承认他制造的即成事实。周围诸镇五道并进,讨伐泽潞。就连素为“反赋之地”的河北也因为有张仲武抚其后背而动员起来了。战局进展甚至比宪宗皇帝多年前在淮西令人怀念的胜利更加顺利。反对派们本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为昭义固然与河朔三镇情形有异,却也不同于其他藩镇:桌面上原因是刘从谏的父亲刘悟在宪宗征讨平卢时不无微绩,而且昭义世袭在宝历朝已经开了先例;冠冕的话语后面另一真实原由是刘从谏在甘露之变时曾给予身在凄风苦雨中的文职官僚集团以声援,并且至今还庇护着若多惨遭荼毒的名门后裔。所以,他的家族在文职官僚集团中不缺乏同情。可这些都没有影响中枢机构在李德裕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转入战时状态。对于从长庆元年起就习惯于官僚集团内部蚁斗蜗争的朝廷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它反映了皇帝与李党结盟在长安的政治生活中正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它使朝廷在泽潞取得了酣畅淋漓的胜利。
我要十二万分地肯定,不,赞美这大气磅礴的会昌年代!
所有人都以为王朝的生命力从根底里萎缩、溃烂、甚至是风化。可是,就在距离惨绝人寰的甘露之变不过数年后,一个人用他遒劲的生命意志捶挞着一个疲敝的时代,使那个时代忧郁、惶恐的单色里猛然间变幻出了教人瞀眩的色泽、奔放的璀璨,从最深的黑暗里迸射出最狂烈的光芒来——对那些武断地夸大了甘露之变破坏力的论断来说,至确至刚的会昌政风是一个强有力的反证。没有李德裕,没有他的睿智和霸道,他的无所不能,谁都以为王朝已无可挽回地唱着挽歌,走向死亡;谁又能知道,无疆的动变原来还可以这样发生。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这样的天才百年一出。出了这么一位,那一百年就有了值得炫耀的资本,为等待这么一位人物所度过的荒凉时光立刻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回鹘的马嘶人吼不再可怕;泽潞和它以东那些更加张狂的藩镇似乎也渺小了、尪弱了,不是不可以解决;即使是那些宝象庄严的佛陀也可以被一道诏令拆成若干碎片——没有超然万物之上的偶像可以用怜悯的目光来审视那个时代。有的,只是政治强人,是李德裕。他也有过平庸的时候,象那些猥獕的官吏一样沉沦于无休止的钩心斗角中,说着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做着不知有用无用的事,在应酬中消磨掉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的时间……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会向陈陈相因的保守作风妥协了。芥视宰相武元衡时他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亢声宣布“骡马不同行”时他年少轻狂。现在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在这个年龄段,《祭十二郎文》里的韩愈都是一副“视茫茫,发苍苍,齿牙摇动”的衰朽形象。可生命恰恰要在垂垂老去的时候无保留地展示出它本身最有力度的成熟美来。李德裕终于决定把一个机会演绎成一段大喜大悲、起伏跌宕的人生;决定以一个教人倾倒的姿态出现在没有大帝可以膜拜的时代。
我记得有一首七绝以自画像的形式勾勒出了这种姿态:
内宫传诏问戎机,
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
月中清露点朝衣。
李德裕的这首诗格调确实不算高。以含蓄论,它甚至不如上官仪的《入朝洛堤步月》——它们同样出自得意倨傲的宰相之手。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那自夸自赞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孩子气。就象是一个孩子,刚刚做了一件很露脸的事情,唯恐旁人不知晓似的到处宣扬。忽然又省悟到自己好像有些得意忘形,于是在后两句中极力地抑制住兴奋压低了声调,可终究还是留下了点清亮的尾音。诗行洋溢着活泼泼的气息,实在很难想像是从一个在宦海中颠簸多年的老者口中吟出。但是,那种志得意满也已经到了高度饱和的地步了。
再多一点,就是虚妄。
无论是否认同李德裕的政策、能力和作风,多数人歙肩俯首,纷纷作了李府门前车马客。大小官员的书剌在李德裕的面前云飞雪落。无数依附者带着多方求取的宝玩,费尽心计侧身相府小斋。那里有水浸白龙皮带来的凉爽,更有权势发散出来的炙人热度。璨然的暖金带、避尘簪含糊地映出一张张谄媚的笑脸,万里外汲来的惠山泉冲泡的茶汤里多少羼和了些许市侩风味……李德裕的府邸位于安邑坊东南。按照唐朝最有名气的卜者桑道茂的观点,风水上讲那里是一只玉盌。那么玉盌里一定满盛了长安官场的五光十色,带着浮沫和渣滓。就连远在洛阳的平泉庄,与其说是为元老重臣日后归隐而筑的心灵家园,毋宁说是宰相铺陈滔天权势的另种场所。“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雁翅桧、礼星石、海州的鱼骨二丈五尺八……鸣皋山下无所不有。园中两座亭台被毫不谦虚地命名为构思亭和伐叛亭。李德裕已经轻狂到用土木砖石自旌功业的地步了。可繁庑的楼台花木中所享受的,也不过是过分喧哗中的一丝寂寞。
一丝寂寞里没有让他听见不绝于耳的怨詈之声。那是切切秋虫,那是预告秋和冬的声音。
刘谏的首级已为李德裕的政治建树安上了壮美的拱顶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想到当一颗红如桃实的流星拖着烛地的尾迹从紫微横贯而入时,李炎驾崩了——飨国不过区区五年多。李炎在会昌五年秋后心火炽腾的症象让人联想起二十五年的宪宗。和宪宗一样,他的早逝和皇室对炼丹术由来已久的迷信有关。对有绝大抱负的李德裕来说,五年时光实在太短暂了,远不能将他胸中的宏伟构想付诸实施。红槿,未来将在前往谪地的驿路上吟咏过的一种花期很短的南国葩卉,正是他政治鼎盛期的绝好象征物。
李德裕苦心经营的事业在李炎驾崩后顷刻瓦解再一次说明——最近的两次是元和宫变和甘露之变——在官僚制帝国中,任何积极的政治进取如此的脆弱。在构建强大中枢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皇帝。其他任何人,无论其个人能力多么强,都面临着和李德裕一样的问题:提防、排挤与不配合,以及广泛的舆论压力。因为他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在传统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是缺乏合理依据——这样的依据只给予皇帝本人。继武宗李炎君临天下的李忱知道这一点。他对李德裕怀有恶紫夺朱的心态并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对李德裕的实际打击。他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在庙堂上下,在九城内外,李德裕实在为他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而这正缘起于他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直接——在操作上而不是制度上——颠覆了中唐以来翰林、枢密、中书门下三权制衡的中枢行政体制:
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自开成五年尽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李德裕对权力的欲望似乎永不饕足,这使得他同僚们备位伴食而已。不仅相权集于一人之手,内廷也感受到来自李德裕的压力了。由于枢密使个人的软弱,这个职位不复王守澄在任期间的风光,出纳王命的权力被暂时地削弱了。李德裕还咄咄逼人地染指翰苑。按照多少年来的惯例,朝廷的外制文书出自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之手,而内制文书则由名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草拟。可从现存文献看,李德裕明确亟请翰林学士照自己拟定的内容撰写诏书就有二十八件之多。他一如既往得到了皇帝的坚定支持。在最重要的诏书起草过程中,李炎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这意味着学士们丧失了利用草诏参预政务的权力,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翰林学士,尤其是承旨学士的失落与觖望可想而知。无怪乎会昌一朝的几任承旨学士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对李德裕的构陷。其中,就有白敏中——他能进入长安政治核心圈子归根溯源得益于李德裕的推荐,否则皇帝原本更青睐他的从兄诗人白居易。然而在李德裕失势的日子里,是白敏中往眢井里投下了最重的一块石头。井底,铩羽涸鳞的李德裕望着头顶坠落的千斤石无奈地感慨道:
唯以怨报德为不可测。
这又岂“恩怨”二字了得。
柳仲郢在地方上切实地贯彻了李德裕“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的政治主张,试图遏制日渐膨胀的官僚机构。由于方志编撰晚至宋代才有,现存唐代史料对京畿之外的情形总体上又是漠不关心的。我们无从得知裁汰州县冗员到底在长安以外给李德裕又增添了多少冤家。可是,以后的几个朝代里却有不止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类似行为绝对会给当政者个人徼怨、徼祸的。
修史一向被看作标志文职官僚集团独立和独特地位的一项工作——所有发生过的,靠他们存留;所有不该发生的,靠他们忘却;他们可以通过修撰历史来重塑历史,使历史成为他们所奉行的信条的图解。修史使他们获得了近乎最终裁判者的权力。可出于个人目的和家族名誉,李德裕还是侵夺了他们的最后领地。一部《宪宗实录》被删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连掖庭宫也投下了李德裕的阴影。他在会昌五年毫无必要地运用他的影响力阻止深得李炎欢心的王才人当皇后——大臣有效地干预册后最近的一例发生在开元十四年。两件事情不可相提并论:玄宗立武惠妃为后势必勾起文职官僚们对武周恐怖统治的痛苦回忆,所以侍御史潘好礼的反对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响应;王才人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企图对政治生活施加不应有的影响,后来她的殉节更是赢得了普遍的同情。所以,李德裕因这个女子寒微出身而反对她晋位带着一点任性,无法让人心服。
我之所以要对被李德裕侵犯了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详尽的罗列,就是试图勾勒出李德裕手中权力膨胀的程度——那是会昌一朝政治实践成功的保证,也是失败的祸苗。连李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也开始对李德裕颛权作风有所不满了。设若赵归真的丹药无害,我怀疑李炎对李党无保留的支持也近尾声了。正是在手中的政治权力无限制地扩大的同时,李德裕使自己的政治空间逼仄到了极点。看起来,在整整五年里,他似乎比任何一个对手都更为强大。但他永远不会比作为全部对手总集的对立面强大。如果说原先文职官僚们对李德裕还处在既恨之咒之,又求之依之的矛盾心理状态,那么在不满李德裕的杜悰、崔铉一齐罢相后,前种心态占了上风。
愤懑的人愤懑地愤懑着。
要颠覆一个集千百样矛盾于自身的大臣,现在缺少的是时机。李炎晏驾使这样的时机来得比预期的还要早些,而给李德裕致命一击的力量掌握在那些被阉割的魑魅魍魉手中——他们仇视李德裕,因为五年来他们的权力不断地萎缩:枢密使的地位削弱了;监军宦官的权力也暂时性地被李德裕遏制住了;宦官势力的领袖和象征仇士良试图煽动一场针对李德裕的宫廷游行,这个魔鬼式的人物曾在那么长时间内主宰长安并肆意摧残文职官僚集团,现在却被迫休致;占据上风的李德裕还曾致力于解除宦官的兵权、财权和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特权,也取得了些许进展。当然,他终究没能改变阉寺对神策军和内库的把持——这不是在短时间内做到的,因为那是宦官势力的命脉,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捍卫的。但是,这已经够了。李德裕所作所为已足够引起阉人们一致的敌意。在李炎大渐的时候,反击围绕着立嗣展开了。
一个李炎所指定的继承人很有可能继承他对李德裕的信任,一个尚在冲龄的新皇帝或许会使权相处在特别有利的地位——这些都不是李德裕的对手们所希望的。他们必须抓住帝位交接的机会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李炎晏驾时长生殿的情形疑云重重。蛰伏于宫闱中的阉党毫无滞碍地出入禁中,别有用心地传达上意。无论所谓的“遗旨”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内心蒿然的李德裕也只能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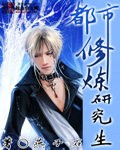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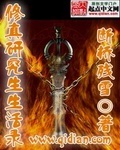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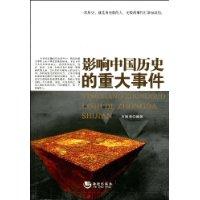
![(历史同人)[快穿]后妃记事簿封面](http://www.667zw.com/cover/13/13881.gif)